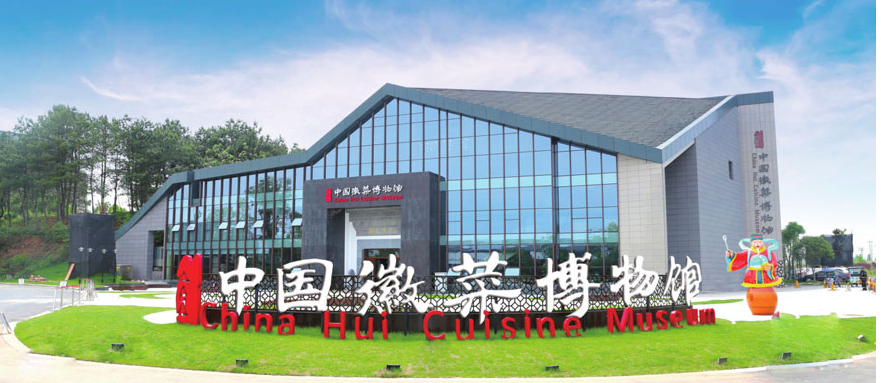徽州境内山势峻峭,古时人来货往,多穿山越岭,走山间羊肠小道。明万历《歙志》载:“古道出入谷间,无跬步夷旷,险绝处高则架木为栈,低则垒石为塘(路)。因其与兽蹄鸟迹相交,故称为鸟道”。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徽商兴起及徽州社会的蓬勃发展,各方捐资筹劳,就地取材,开山采石,垒土砌磅、铺设台阶、逐步“硬化”路面,形成以古徽州府(歙县)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
大洪岭古道为“徽安古道”(古徽州府至安庆府)最险要路段,是古徽州西南部北上的主要通道。它南起祁门县大坦乡大洪村燕窝组,跨越大洪岭,至祁门县安凌镇雷湖村,全程约8公里。古道始建年代已无从考据,初次铺设石板为明万历年间(1573-1619),由祁门孀妇郑氏捐银修辟。清道光三年(1823),祁、黟两县士绅捐资六万,历时六载,再次开山凿石,更曲为直,化险为夷,拓宽至丈余,从此,大洪岭险道变为坦途。如今,在众多残存的徽州古道中,如此宽阔、平整的登山官道已绝无仅有了。
大洪岭因山势陡峭、常有山洪奔泻而得名,主峰“望江尖”高1126米,登高远眺,可及长江浩渺烟波。近年来,因其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而声名远扬,在山花怒放的季节,盘旋在大洪岭上的青石古道宛如一条五彩长廊穿行在花海中,从祁门县城到大坦乡的公路也因此被赏花者的车流堵得水泄不通。
我没赶这个热闹,只在这万物凋零的寒冬才首次造访这条美丽的古道。
从祁门县城往北转入大坦乡方向,并不宽阔的乡村公路空荡荡的,20多公里行程,未见几辆汽车来往。
至峡谷深处,路边一块巨大的山石上刻有“阊·昌江源”几个大字,“阊江”为祁门境内最大河流,源于大洪岭下,入境江西后则为“昌江”。一江清水出万山,确有破“门”而出之感,改“阊”为“昌”,恰如其分,不得不钦佩古人为江河命名的睿智。
打开车门,一股寒气袭来。已过“大雪”节气,山区入冬已久,虽未降雪,早晨气温还是降到了零度。路边枯黄的草叶沾着一层银白的霜花,田里的油菜叶已冻成酱红色,坡地里的油冬青却更显黝黑发亮。
不同的植物在这个冰霜寒冷的季节里不期而遇,色彩只是它们生命繁衍的过程而已。
将这一岁一枯荣的生命活动嵌入到历史的年轮中,一切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将浓缩成一个周而复始的轮回。古道起点的燕窝村,十来户人家,路边房屋刚“改徽”不久,齐刷刷的马头墙,洁白的墙面,却也遮挡不住那些早已辟为菜园的房屋旧址。当年这个大洪岭下商旅络绎的山村,如今也像寒冬中的植物一样,静寂在岁月的轮回中。我们脚下这条穿过各家门前的水泥路,早已不是当年店铺林立的“枫林街”了,那块“省会通衢”的题额也不知所踪。
只有村头那座石拱桥定格了历史的节点,它仿佛一个时光的开关,一头连着现代的水泥马路,另一头接着数百年前的青石古道。
桥下这一溪清冽的甘泉,从远古流淌到现代,千万年不变地潺潺着,使这座小小的石桥成了阊江源头第一桥。巍峨宽阔的大洪岭从天际边流淌到这个狭窄谷底的拱桥下,孕育了奔流而去的阊江。
有了水,大山的刚烈、古道的沧桑都变得温婉起来。桥头那块刻着“大洪岭”的石碑似乎刚立不久,青涩的凿痕还未接受岁月的洗礼,与脚底下戴青色的路面形成鲜明的视觉反差。
古道以青麻石铺设,虽经两百年风雨侵蚀,路面也还基本平整,部分石阶已有塌陷错落,但依然不失当年修筑时的“高规格”:台阶宽约五十公分,高约十公分,长两米有余,弯道处可达三四米。古时官轿、脚夫均可自由往来行走,全然没有“鸟道”上战战兢兢的窘迫。
在每条徽州古道中,几乎都有“十八拐”概念,即山道以Z字形从山底盘旋至山顶的“十八”个弯道。有民谣云:“大洪岭,如巨蟒,上七下八十五里,钻云破雾八十一道弯……”。大洪岭古道上宽阔的台阶和几十个迂回的“拐”夷平了峭壁的坡度,让千米登高如履平地。“十八拐”自然成了徽州古道的图腾,这一古人的智慧在现代交通设计中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芒,徽州人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或许就是受到“十八拐”的启发吧?
如今,这七拐八弯的山道上,当年的青麻石已成黛青色或黑褐色,方方正正的石板已被磨去尖锐的棱角,山坡上的朽木桩长满绿茵茵的苔藓,密密麻麻的竹林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历年倒下的枯竹,路面上刚落下的五彩秋叶覆盖了石缝里已化作春泥的尘土,只有那些左突右张的“拐”依然坚强地盘桓在这高耸的大洪岭上,支撑着这条通往远方的古道。
沿着山脊迂回到岭头后,一段平坦的道路穿行在山垅间。刚才一路攀高,一株株大大小小的映山红树一直簇拥在道路两边,并不浓密的叶片已染上绯红,并随着山风的吹拂零落而落,它们终将化作春泥,去滋养来年的绽放。
此刻,我却在千米之巅,在这凛冽的山风中,惊喜地邂逅了一丛反季节盛开的映山红。虽然没有春花的娇艳,没有绿叶的衬托,没有连片的花海,但在这蓝天之下,在一片干枝枯叶丛中,它却显得格外清冷圣洁。
一株映山红点亮了一个季节的记忆,古道垭口上那些残垣断壁,却坚守着一个时代的印记。
垭口和古道一样宽敞,足有两三亩地,只是其中的建筑仅剩下千年不腐的石墙残基。清道光年间修建的碑亭也早已圮塌,那十二快刻印着先人功德及护路禁告的碑墙终于失去檩椽瓦片的呵护。
任由风吹雨打的碑石,如今已毁损近半,残存的几块就像风烛残年老人廖寂在这荒山野岭上,终日翘首期盼着亲人的慰藉。
碑亭虽垮,亭柱上的嵌字楹联依然回响在这绵延起伏的大洪岭上。
“大地回春,从鸟声喧飞巧燕;洪山耸秀,万龙翔集似闻雷”,
对联头尾巧妙地嵌入大洪岭、燕窝、雷湖这三个地名,又描绘了这群山耸秀、飞鸟鸣瀑的瑰丽景象。
徽州山峰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山南秀美,北坡险峻。和南面山脊上平缓攀升的古道相比,山北的道路是在山凹里呈S形急促下行的,让我们的返程增添不少强度。
好在下午的天空变得清澈起来,我们再次回到垭口,攀上大洪岭峰顶,极目远眺,远山近壑,村庄道路,一览无余。
古往今来,登高望远,总让人感慨万千。
大洪岭古为祁门、黟县、石台、太平县界,亦为三方分水岭,雨水往北经石台入秋浦河,往南过阊江入鄱阳湖,往东南入青弋江,三者都将汇入长江,最终奔流至东海。
同一方清水,必将殊途同归。
人却不然,当年的同学战友小伙伴,同一起点出发,如今却各自走在一条永远无法汇合的路上,甚至被分割成遥不可及的阶层。倘若有一天有幸汇合在一起,或许早已归于尘土。
行走山野,问道先贤,顿悟人生,或许就是徽州古道的情怀所在吧?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