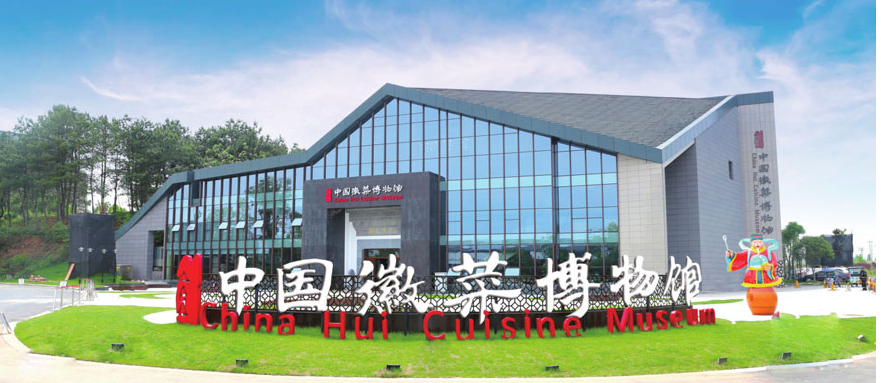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古时道路多为羊肠小道,明万历《歙志》记载:古道出入谷间,无跬步夷旷,险绝处高则架木为栈,低则垒石为塘(路),因其与兽蹄鸟迹相交,故称为鸟道。明弘治《徽州府志》记载:自睦州青溪县界至歙州,路皆鸟道萦纡。
此处所称青溪县界至歙州的“鸟道”即为贤源岭古道。
青溪为古县名,现浙江淳安县境内,故治已淹没于千岛湖中。古时徽州至严州府(府治今浙江建德市),水路虽可通达,但新安江水急滩险,环山绕水,路途遥远,人员往来,陆路更为便捷。从徽州府出南门,过紫阳桥,经雄村、森村,往东南越贤源岭、长标岭、万岁岭或歙岭可达遂安县、严州府,远地连接衢州、金华等地,是歙县南下的通衢孔道。
歙县南部峰峦叠嶂,山高林密,古人穿山涉水,走出一条南下通道实属不易,今年初夏,我曾走歙岭,寻觅朱熹题写的摩崖石刻——“新安大好山水”,未果,却遭遇“马小姐”(蚂蟥)“围攻”。徽州南部的白际山脉山瘠水剐,但植被稠密,山地阴凉潮湿,蛇蚓横生是自然而然的。户外行走,遇上几枚蚂蟥无伤大碍,倒是附近的贤源岭、万岁岭两条古道时有毒蛇出没,路边草蔓箬叶,青蛇缠绕已司空见惯,夺命“五步龙”也偶会盘踞路中。因故,挨到深秋万物凋零之际,我们才去探秘歙岭北段的这条“鸟道”。
贤源岭古道自歙县森村乡皋径村起,跨越海拔810米的贤源岭,过贤源村,至长陔乡长标村,全程约10公里,大部分石板路面保存完好。继长标村前行,到长标口便分两路,南行过歙岭至遂安,东南过万岁岭(谷雨岭)至淳安、建德。当年朱元璋在璜蔚村兵败陈友谅后,就是在谷雨岭上屯兵修整的,并经此出发,攻占淳安、桐庐、金华,占领杭州,建都南京。
前几天,一直秋雨绵绵,天气预报显示,下周也是阴雨不断,本周六多云天气,像是在秋雨缝隙里挤出的一线蓝天。早晨,地面上还是一滩滩水凼,晨风夹杂着雨雾,黏在肌肤上,凉丝丝的。从屯溪出发,我们的汽车蛇行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环山绕水约四十分钟车程,很快钻进山坳尽头的皋径村。当年这个“大路边”的“岭脚村”如今规模依然不小,两山夹持间,一两百栋崭新的钢筋水泥楼房傍溪而建,偶有几堵斑驳的马头墙佝偻其间,显得格外孤独,苍老,在这里,当年人来车往所留下的岁月痕迹离我们已渐行渐远。
我们在村中驻车后沿贤源溪边步道向山中行进,当年的青石板已被平整的水泥路所覆盖,仅有一座挂满青藤的单拱石桥还连接着那段古老的历史。热情的村民告诉我们,公路已修到山脚,里面还有个停车场,可以直接驾车进去,不需要走路步行的。
宽阔平坦的公路覆盖了青石古道,方便快捷的汽车代替了双脚远行,这是人类几千年孜孜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却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去行走一段青石步道,去探秘一条基本丧失交通功能的古代通衢孔道,是很难被这些将汽车视为“美好生活”一部分的村民所理解的。两年多来,我们背着行囊,行走在村庄,徒步在山野,总会迎来异样的关注,也收获了乡民的淳朴。
走出村庄数百米,果然有一水泥浇筑的停车场,可停放一二十辆车,此处既无村民居住,也无其它生产生活设施,难道建这么大的停车场就是方便我们这些行走者吗?如是这样,这条古道应已修整过了,或是常有人行走的,至少不会草蔓丛生。
过了停车场,绕过一道山脊,是一座路亭,即古道起点。悬山式古亭依山临路,贤源岭流下的溪水从亭前潺潺而过。在徽州古道上,这类路亭叫“岭脚亭”,商旅脚夫沿着山坳行走至此,往往要走进路亭,在两边的石凳上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积蓄点力量,然后开始拔高登山。
过了路亭,古道向山坳深处蜿蜒前行,随着山坞的深入,却发现古道并非我们想象的已修葺规整,路边的梯田已撂荒多年,两边的箬叶、柴草几乎遮盖了路面,“鸟道”之名恰如其分,要不是秋天草木枯萎,行走这样的山路是很危险的,轻则被草叶割破皮肤,重则与蛇蝎相遇。
一般说来,这样荒芜的古道,路面塌陷毁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实际状况却出人意料,当我们沿着溪谷行进数百米,并向山脊拔高,一直到垭口为止,整条古道基本保持完好,即使常年受到山洪冲刷的水沟边也不例外。究其缘由在于古道特殊的垒砌方法,即在每一块平铺的青石板之间、每一阶台阶前嵌入一块竖立的石块,像一堵深入地下的挡土墙挤压着每块路面石板。这样山道,即使建在陡峭的坡道上,或是靠着湍急的河流边,出现少量水土流失或外力冲撞,也不至于影响路面的稳固性,甚至还会增加石块之间的咬合力。
在徽州古道上,古人的智慧还体现在路径的选址上,徽州周高中低,群山环绕,越境古道几十条,境内便道不计其数,但每条古道走向基本都在两点间的直线上,且所跨越的山岭也是附近最低的垭口。另一方面,古人建设山道时,几乎都能巧妙地避开悬崖峭壁或陡山峭坡,确需经过的陡坡,也能因势成形,利用Z字形盘道来降低路面的坡度,让肩挑背驮者安全顺利地跨越每一座高山大岭,于是“十八拐”便成了徽州古道的图腾,它将古徽州人的智慧和坚韧深深地刻印在茫茫大山之中。我们脚下这条从山底登越贤源岭古道,几乎都是在山脊上迂回而上的,它将高耸的山岭切割成平缓的蹬道,像一条舞动着的丝带跌落在贤源岭上,如果航拍下来,其壮观程度不亚于著名的“24道拐”景观。
“柺”到山岭尽头是贤源岭垭口。垭口平坦,一亩见方,左有一坍塌的路亭遗址,对面是一条“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的小路,通石耳山,每年映山红花开季节,可从此处登山赏花。路亭废墟上残留一截倒落在地的石碑,部分碑文尚可辨认:
“供奉:龙虎玄壇赵大元帅,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尊,█界█地█福德██”
眼前这块石碑是我们一路走来唯一获悉的文字史料,遗憾的是碑文没有落款,无法确定立碑时间。我从网上查询得知,“龙虎玄壇赵大元帅”是道教护法四帅之一,初为恶神,明以后被道教奉为财神,其信仰普及民间。观世音菩萨是家喻户晓的,以此推断,古时此处应为一处庙宇,供奉几尊菩萨,护佑来往商旅出入平安,祈盼生意兴隆。如今菩萨也自身难保,没留下一点残渣碎片,只有这半截石碑还在这里坚守着曾经的喧嚣。
我们在路亭门口小憩后继续前行,过垭口沿南坡下行。
下坡的路比较平缓,或是刚才一路攀高,来不及欣赏身边的风景,此刻才发现整片山野已层林尽染,铺天盖地的秋色充斥着整个视野。
我一直认为徽州的秋色是一种独有的风景,是特有的地理环境,特定的植物种类,特殊的日夜温差造就的。她的美不是“层林尽染”几句苍白的文字可以描述的,荒山野岭中的一丛灌木,就能点亮蓝天下一片绚丽的色彩,房前屋后的一树灯笼柿,就把黑白徽州点缀得让人心动不已。
还有哪个季节的色彩能够将徽州山村的宁静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呢?我每次行走在斑斓的山野中,暖秋的色彩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总会激发我内心的一份感慨:
徽州的秋,是上苍的赏赐!
从贤源岭到贤源村不足一公里,我们穿行在丛林中,薄薄的秋雾与姗姗来迟的阳光在树叶间的缝隙里缠绵着,一条细细的光束跳动在猩红的枫叶上,像一面红色的镜子,折射出晶莹的光亮,忽而又被瞬间而来的一丝微风吹跑了,像一个调皮妩媚的小精灵,挑逗着路人荡漾的心襟。招人欢喜的还有那些挂在藤蔓上的猕猴桃、树丛中红透了的山楂,以及路边那些不知名的红果子、黄果子,玛瑙似的……
贤源村位于贤源岭下,海拔近700米,村庄屋舍沿一条清澈的小溪排列着,并向两边的山坡层叠而上。黄色的土楼与粉白的现代楼房挤在一起,村庄中青石台阶与水泥路面交织着,古石桥边那棵枯树新枝的千年红豆杉与树底下的山花相看两不厌,还有闲坐老屋前、古道边的几位老人,他们或许正在闲聊着这条古官道上曾经发生的故事……
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即使这天高皇帝远的小山村也蕴藏着浓浓的文化味道,古道起点的“皋径”,“皋”通“高”,指水边高地,意为傍水而行的道路,以此作为一个山村的名字,确有一种高深莫测的味道。“贤源”二字本身就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气息,还有5里路外的长标村,史上竟出过一个进士,那座“进士第”就足以标榜这个山村的文化底蕴。
从贤源村到长标村的路宽阔平整,如古人所称的“鸟道”至少也是“鸵鸟”道。当然,“鸟道”仅是山道险峻的揶揄而已,贤源村在行政上隶属于长标,公路开通前,这条山道是贤源人出入的主要通道,即使现在,乘坐公共交通者,也还只能到达长标,然后步行翻越长标岭至贤源。因常有行人,这条横穿山腰的路整洁规整,我们轻松舒坦行走二十多分钟,即到达长标岭。
和其它古道垭口上的建筑不同的是,长标岭头建有一道拱门,高约3米,宽约1.5米,深近3米,由凿磨平整的块石垒砌而成,门楼转接成拱形,拱顶裸露在外,未加建任何建筑。这道拱门既非残留的古城门,也非路亭过道,而是一处独立完整的古建筑,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
建造此门用意何在?
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拱门斜对面一片重叠排列在山腰上房屋就是长标村,村庄四面环山,唯东南方向有一峡谷豁口,古人认为此为“白虎口”,即“风水”所说的“犯白虎煞”。白虎煞为凶煞,轻者破财,重者血光之灾,这是一个村庄不能承受之重。古人在这正对“白虎口”的方向建造此“门”,实为“青龙洞”,以破解此“凶煞”。长标这个偏居深山的小村,数百年人丁兴旺,文风昌盛,难道就是这道拱门的造化?
在古徽州,不管是村庄布局,还是建屋造房,都很讲究风水。我对此毫无研究,只知每次走进一个视野阔达、阳光充足、溪水潺潺的村庄,都有一种让人神清气爽的感觉,这种自然气流与山势走向结合,让人感到身体通泰的人居环境,或许就是古人所追求的“风水”吧?
过了“青龙洞”,前行十多米是一座路亭。路亭位于峭壁之上,下行这段陡坡的古道成了我们今天行程中最养眼的一段。因为山坡的断崖式下降,这条近两米宽的石阶路面在这里绕了两个精美的流线型弯道,将徽州古道的磅礴和柔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遗憾的是这段古道不足百米,其后一直到村庄,全部是用水泥浇筑的台阶。水泥台阶平实规整,却少了青石的韵味,也湮没了历史的沧桑,我不禁要问:
这样的水泥路面能够百年不损、千年不毁吗?
也许数十年后,这些扛不住风霜雨雪侵蚀的水泥,早晚会在岁月的年轮中飞灰湮灭,被它覆盖着的青石路面也终将会重见天日。
沿这段水泥台阶下行不到十分钟,即抵达目的地长标村。我在村中转了一圈,未见“进士第”,问询村民得知,古宅常年失修,濒临倒塌,终在建造小学时拆除了。
在这地无三尺平的山腰上,一座进士第让位给孩子们读书,也算是找到了归属,但在我心中还是产生了那么一股如鲠在喉的酸楚。
在村中,我们还找了几位老人,想了解这条“鸟道”的修建历史,均无所获。返程时,从贤源村一位老人口中得知,在贤源岭的山腰上有座塌落的路亭,内有一石碑,详细刻录了这条古道的捐输善主。
返程时,我们找到了这座古亭废墟,却未见石碑,终未获知这条古道的生辰八字。
在这座曾经记载着古道历史的路亭遗址前,我静默了片刻。
一个“停”字瞬间在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亻”在“亭”边,不就能“停”下来歇一歇了吗?如今梁塌瓦落,“亭”倒了,“亻”就停不下来,被飞速前进的现代生活追赶着,为名为利为了那些周而复始的事务而不停地向前奔跑着……
今天,我们逃离喧嚣,在繁忙中挤出一丝闲暇,将疲惫的身体塞进徽州的金秋里,让心沉浸在暖融融的色彩中,不就是在自己心中搭建一座路亭吗?一座能够让我们身心暂时停下来、歇一歇的路亭吗!
2018.10.20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