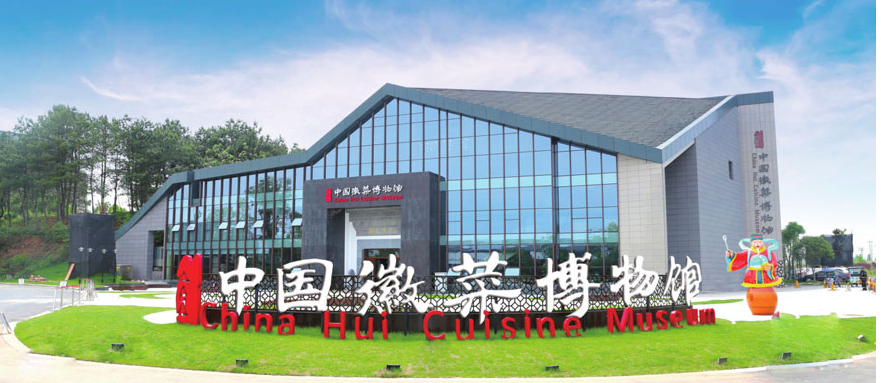如果说徽州乡村的秋色是一幅线条明晰、色彩错落的水彩画,秋风岭则是漫无边际、随意挥毫泼墨的油画,一幅疏密相生、浓淡相宜的 画卷。
周六早晨大雾。
初冬的大雾。
徽州的雾比天气预报准确,冬雾之后必是晴空万里。
相对于春天的潮湿、夏日的闷热、冬季的湿冷,徽州的秋天是体感最舒坦的季节,不冷不热,不湿不燥,从九月末到十二月初,即使过了小雪节气,也还一直舒展着秋日的爽朗。而今年秋天,却是例外,整个季节都淋着淅淅沥沥的雨,甚至到了十一月份,还惊出几声闷雷,把美妙的秋韵震得支离破碎。
这两天,久雨逢晴,整个城市突然亮堂起来。
只是街边行道树上的叶子经不住秋雨的纠缠,匆匆忙忙地结束了这一岁年轮的旅程;大大方方的马褂树上,叶子青的青,黄的黄,也在纷纷飘落,等不及霜雪的迎送就谢幕了这一季的色彩;新安江边的银杏树早早进入冬季,树梢上倔强地伸举着光秃秃的枝条,底层的几枝树丫上还缀着一圈黄灿灿的叶子,像条迷你裙,穿在一群正在卸妆的舞蹈演员身上,不伦不类地在晨雾中婀娜着。
徽州的秋天是很长的,准确地说,秋色的余韵拖得又宽又长。这个周末,在徽州西部的秋风岭上,这样绵长的秋韵装进了我们的行程。
清晨,我们钻进浓雾,驱车出发。上高速,过县道,穿行乡间小道,行程百余公里,到达秋风岭下的际上村。
在这座几十户人家的山村里,太阳刚把晨雾收拾妥帖,整个村庄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懒洋洋地伸着懒腰。来不及散去的炊烟还袅绕在村庄上空,朦胧着田野和远山。
和城市相比,初冬的山村更显宁静,空灵的田间地头已少有农人劳作。在这些绝大部分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村庄里,这个季节只有三三两两的留守老人,蜷缩在这个他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山沟里,慢慢地消耗着暮年的时光。在这个静默的山村里,房前屋后,大路小巷,似乎连空气都是静止的,偶有一两个小孩打闹,一两声鸡鸣狗吠,也不再是那种肆无忌惮嘶鸣喊叫,似乎连他们也融进了这种日暮般的静谧里。
对于久居城市者而言,偏僻山村总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感。面对我们这群开着汽车、背着行囊的陌生面孔,这些寡居山村的空巢老人,他们内心那份久违的好奇和骚动也瞬间苏醒了过来。
在和村民的攀谈中,我们得知这个“际上”名称的来历。
徽州山村名字一般随手捏来,无外乎属地属人属事,“际上”似乎有些列外,乍一听,深不可测,不知所以。
新华字典解释:“际,交界或靠边的地方;彼此之间;时候……”
古时际上属徽州西北边陲,翻过村后的秋风岭就是池州府石埭县(现石台县)地界。按老人介绍,“际上”即为“边界上村”,顺水而下,与之相隔数百米的“际下”则是“边界下村”。这样的山村名字,简单明了,寥寥几笔,却底蕴深厚,令人惊叹。
徽州村庄讲究依山临水,即使一个小山村也不例外。秋风岭、百倍岭潺潺而来的两股清溪成了际上村左依右靠的“财富”,其交汇处则为水口所在。祁门历口一带北上的古道在此兵分两路,一路前往百倍岭,为礼佛祈愿之路;一路翻越秋风岭至安凌镇(古时属石台县,1965年划入祁门县),往池州府,远地可北上京都。
秋风岭位于祁门县古溪乡与安凌镇之间,曾是徽州府与池州府的界岭,因处三县交界地,为历代兵家据守要塞。现存秋风岭古道南起古溪乡谢家村际上组,北至安凌镇联合村田许组,路面宽1-1.5米,全长约八公里,基本由就地取材的青石拼砌而成。在众多徽州古道中,这样的建造标准只能算是一条低规格的“乡道”。
古道从村口出发,缘溪而上。
和古道并行的是从秋风岭流淌下来的清澈溪水,山谷的自然落差在这里形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潭。错落的水潭间连接着一簇簇银白的水瀑,如帘,如柱,如虹。水瀑跌落在水潭里,激起一圈圈涟漪,在太阳照耀下形成粼粼波光,闪闪烁烁的,如梦幻一般。在这碧水清波下,还游弋着许多小鱼,如一片片柳叶在水中飘动着。在这高山水潭里,这些鱼儿经历多少山洪,飞跃多少瀑布,才抵达这人迹罕至的深山水潭里。他们就像山中修行的隐者,在这清泉剐水里过着清贫自在的生活。因与尘世俗缘隔绝得太久,只要有人靠近水边,他们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
随着古道的不断拔高,溪谷也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巉,倾泻而来的泉水挤在崖石夹持的凹槽里,形成一条宽窄不一、蜿蜒崎岖的瀑布,汹涌澎湃地向山下奔腾而去。
世间万物总是相通的,山里的小溪也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从“树叶”到“枝条”、从“细枝”到“树干”,滴水成泉,泉溢成流,众流汇聚,奔流成河。约两公里后,小河缩成小溪,最终瘦成淙淙细流。与水流伴行的青石古道在这里也被依山就势的土路所替代,不知是当年没铺设石头路面,还是原有路面已被百年风雨侵蚀殆尽。
如今秋风岭古道“硬化”路面已不足30%。好在该路段已列入“黄山168国际徒步探险基地(线路)”,年年有人打理修整。
“黄山168”是以法国环勃朗峰赛(UTMB)里程和规则为标杆,应用国际先进的线性步道设计理念,融合徽文化因素,串联山脉、峡谷、古道、古村落、湖泊、景区等资源,整合而成的户外徒步探险线路。步道自祁门县箬坑乡出发,由西向东穿越,纵贯祁门、黟县,最终抵达黄山风景区,全长168公里。
古代交通网络在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在古徽州这个独立地理单元里,也仅剩断断续续的片段。在“村村通”等现代交通的冲击下,残存在荒山野岭的青石古道除了满足我们一份惆怅的古典情怀外,仅是一种亲近自然的自恋而已。
行走古道,春赏繁花,夏嬉山水,今天驱车百余公里,穿越秋风岭,或许就是为了寻觅这个“秋风”的意蕴。
在徽州山岭中,少有如此诗意的名字。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取个山岭的名字是不会像现在给独生子女取名那样咬文嚼字的,就如“际上”一样,本以地域为名,只是在现代人看来貌似高深莫测而已。“秋风岭”或许就是此处秋风格外凛冽,山中草木野果比其它地方枯萎零落得更早一些吧?
然而,当我们沿着古道向山坞行进,走进山岭深处时,扑面而来的绚丽还是让我们惊喜不已。湛蓝的天空下漂浮着丝丝白云,红、橙、黄、绿、紫,各种鲜艳的色彩,从山谷一直妆点到山腰,即使已经枯黄的阔叶林也还满树浓密,为这初冬的山谷铺上一层沉稳内敛的底色。行走在古道上,路边随处可见各种野果,红得晶莹,黄得透亮,紫得深邃,即使深褐色的猕猴桃果子也丰腴得让人垂涎欲滴。
如果说徽州乡村的秋色是一幅线条明晰、色彩错落的水彩画,秋风岭则是漫无边际、随意泼墨的油画,一幅疏密相生、浓淡相宜自然画卷。
上帝把最美的色彩给了秋天,秋天只是把一些五颜六色的颜料随意倾倒在这些山岭上。这里漫山遍野的树木、藤蔓,比不得村庄水口的风水树,日日有人膜拜,也不像黟县塔川那些乌桕、枫树,年年四方来朝,更不敢和城市里整齐一致的行道树媲美。它们就像际上村里的那些老人,在这青山野地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即使到了这个瓜熟蒂落的秋季,也能安详在这蓝天白云下,平静地绽放着这生命的绝唱。
此刻,置身在这斑斓的巨幅画卷里,一切言语,一切躁动、一切凡尘纷扰都会瞬间静默下来。是火红,是金黄,还是没有绽放就在连绵的秋雨中凋零而落,都是顺其自然的事,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也会去。芸芸众生,何尝不是这山林中的一枝树木一根草藤,粗细高矮,芽出叶落,只不过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冷和热,不同生活阅历的得与失而已,终究改变不了日月轮回的自然规律。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许正是人和自然万物的相通之处吧?
进入人生的秋季,就该像这些草木一样,学会过着通俗易懂的生活。
相对于一岁一枯荣的树木花草,秋风岭上古战场遗址或许早已被岁月遗忘,任凭春风吹拂,秋霜扫射,也不会再有来年的春天。
我们经过近两小时的行程,穿过秋风岭下一片荆棘丛生、且被野猪拱得坑坑洼洼的盘山蹬道后,到达秋风岭垭口。这里的一座路亭已塌落,连着路亭的古关隘也已圮毁,仅剩块石垒砌的半截关楼。连接关门的是一段石墙,残存的石墙高、宽仅1米许,长数十米,像两只掉了毛的雄鹰翅膀趴在垭口两边的山脊上。石墙南面是相对平坦的山脊,为驻守之地,北面是陡峭的山崖。1860年6月,两江总督曾国藩驻扎祁门,修筑了这些山岭要寨上的工事,在冷兵器时代,这一天险足以御敌于境外。1861年正月,清军江长贵部就是在大洪岭、秋风岭、大赤岭上击败了自石埭来犯的“粤匪”。
岁月无声,惟石能言。这些冷兵器时代留下的工事也见证了一段悲壮的革命历史。
1934年7月,中共祁黟县委迁至际上村,1935年元月,红军皖南独立团及中共石埭县委游击队数百人进驻际上。因叛徒告密,国民党军队连夜偷袭,红军在向秋风岭撤退过程中,不幸牺牲17人,伤200余人,国民党连长也在秋风岭上被红军击毙。
如今,那段刀光剑影的历史早已根植在这段古城墙里,和秋风岭古道一样,也终将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古道北面下山的路已被密密匝匝的箬叶林覆没,无法继续行走。我们一行只能放弃原先的行程计划,沿着“黄山168”新开挖的便道向山脊线行进,继续品味这段古徽州“际上”的初冬秋韵。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