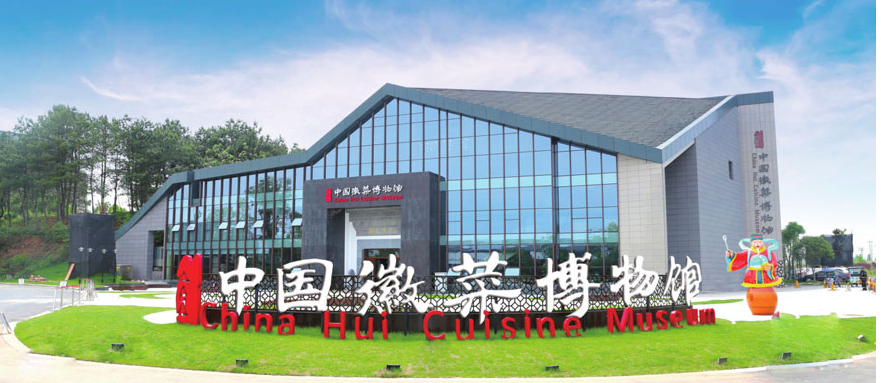大连岭古道为率水河两条支流流域,即板桥乡与汪村镇间的“乡道”。东接浙岭,通达徽墨三大产地之一的婺源虹关。走该道过大连岭至汪村,入溪口,到江潭、山后,在汪村桐子岭并入徽州至浮梁的官道。(全文2800字,阅读时间约10分钟)
古道指数
精彩指数★☆☆☆☆ 危险指数★★☆☆☆强度指数★★★☆☆ 完好指数 50%
休宁板桥古称浙东乡,隶属婺源县,毗邻浙源乡,为婺源进入徽州、东进沪杭的重要门户。古时,婺源的山货等物资从清华出发,跨吊石岭至休宁溪口后,经率水河入新安江,直通杭沪,比走五岭古道省去近百里旱路。其间的官道(吊石岭古道)进入板桥后,沿沂源河峡谷,连接沿途大小村寨。尤为峡谷尽头的樟前、凰腾、梓溪、徐源等村庄,几乎都处古代交通枢纽位置,部分古道至今尚存,如觉岭、浙岭、重龙岭、前山岭、高湖山等。大连岭古道则是连接率水河两条支流流域,即板桥乡与汪村镇的“乡道”。走该道过大连岭至汪村,入溪口,到江潭、山后,在汪村桐子岭并入徽州至浮梁的官道。
“大连岭”因汪村镇大连村而得名,并非古道的确切名称,准确地说,这条跨越大连岭的古道还没真正的名字。在古徽州,南来北往的青石古道交织相连,如今大部分已被公路所替代,那些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上残存的少量步道,也是断断续续的。故按以往习惯,我以这些古道跨越的主要山岭为名,以便记录。
以山岭为名,难免有重名重姓的,如新岭(休宁、绩溪)、塔岭(休宁、歙县)。大连岭也非唯一,我以前已走过歙县石门至淳安浪川的连岭古道,因歙淳之间一条海拔1200米、连绵十几公里的山矼上有大大小小几十座山岭相连而得名,并有“大连岭”和“小连岭”之分。据《歙县志》记载,歙淳“连岭古道”肇建于三国时期,或为徽州古道之鼻祖。休宁境内这条称作“大连岭”的古道既无显赫历史,也非重要关隘,建造规格普普通通,且我只走了部分路段后就改道其它方向,确实没多少可写之处。
然自上次出行至今已两月有余。元月初因雨雪天气不便户外活动,到了下旬,“新冠疫情”来袭,华夏之殇,神州呜咽,以至四面楚歌,人人自危。人类自从直立行走开始,就在孜孜不倦地向现代文明迈进,但与之相悖的那只罪恶之手也始终没有停止过,灾难总在贪婪中无情地酝酿着,终在庚子年初,在这些流光溢彩、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决绝地爆发了。
到了上周,屯溪已连续近一个多月无新增病例,应急等级有所下降,出行管制略有放松,市内人员可以有序流动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走出家门,走进大山。此刻也只有这些从远古走来的莽莽青山,才无怨无恨地接纳我们这些精神疲惫者,就像一位母亲面对浪迹多年、毫无音信的游子一样。
我们驻车樟前村时,自觉带上口罩。在这一个多月里,国人对口罩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弯,从以前远离戴口罩者到现在恐惧不戴口罩者,人性的脆弱和自以为是的劣根在一个薄薄的口罩里暴露无遗。我一介凡夫俗子自然也脱不了这等俗气,但在这些大山深处的村民眼中,我却成了另类,好在没被当成“病毒”驱离。古道入口在村头的茶园地里,与浙岭古道起点的“履安桥”相距仅几百米。当年婺源虹关的徽墨跨浙岭至此,就是翻过眼前这座高耸入云的大连岭,再经汪村、溪口、右龙,出徽州,过浮梁,挺进中原、南下闽粤的。
我无法考据这条古道的肇建年月,如以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履安桥”为据,至今该有150多年了。如今,这些沉淀在低矮茶树下的古蹬道已被挤得又细又长,不再齐整的青石板依然玉润青亮,它们毫无保留地印记着百余年里在它们身上发生的故事:有两脚走天下的徽商,有揭竿而起的红军、新四军,还有两地亲来眷往的乡民。如今,这里的一切都已归于平静,平静得就剩眼前这片茶窠树的细枝嫩杪上刚浮出的一层新绿。
山腰上的一棵老树已有些年头了,现在还没长叶子,细芽都没有。老树的树干已烂出一个长长的疤洞,树丫上还有几股枯枝,风吹可折的样子。古时长在大路边遮荫避雨、百年不枯的树,无非是香樟、苦槠、枫香等,这株虬枝铿锵的落叶老树不是乌桕就是柿子树。树和人一样,苍老到一定岁数,皮肤、五官也就没有多大差异了,个体形貌甚至性别特征也渐趋同。在这山腰的茶园当中,低矮的茶树剪了一茬又一茬,茶叶的清香一年接一年地从这里流淌到远方,也在这棵老树上凝结成百年醇香。百年的风和月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凿刻在这根不再光滑的枝干上,与对面觉岭上跌宕起伏的山峰遥相呼应着。
觉岭飘绕在云天之间,若隐若现。我们早上出发时,还弥漫着浓稠的纱雾。冬雾晴,夏雾雨,这早春的雾或是随心所欲的。此刻,太阳已翻过云层,涂抹在这片黛青的山峦上。山谷里的白雾快速地向山顶撤退,我脑海里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新冠病毒”害怕太阳的话,当朝阳升起的那一刻,它们会不会像一群衣衫褴褛的溃军那样,匆匆向空中逃窜呢?那一定是万民欢呼的壮观场面。登高约二十分钟,古道出了茶园地,进入竹林。过了竹林是茂密的杉树林,上世纪“植树造林”年代种植的徽杉。在高耸玉立的竹木林间,古道显得更加低矮,宽约一米的路面已被枯枝烂叶盖得严严实实的,几乎见不到当年徽州先人千辛万苦铺设的石板。其中一截在山脊下的路段已被茅草灌木完全湮没,路面石板更是不知所踪,如在草木葳蕤的夏季,这路是断然不敢走的,说不定就侵入了野蜂和毒蛇的领地。
约一个半小时,到达“灯宠尖”,临近大连岭。“灯宠尖”是地图上标注的名称,我总觉得应该是“灯笼尖”或“灯盏尖”,不知是当年地图绘制者“音译”方言时生搬硬套的,还是另有故事,我未作考据。板桥一带的方言既有休宁话的词汇,也有婺源话的语调,相当于徽州方言的“六级考试”的题目,真的听不懂。我们从这里离开古道,走一条便道下山,并从另外的山岭绕回到出发点,即所谓的“穿越路线”。
山底是一个叫野猪的村庄。与其说村庄,实际就是五六栋大大小小的老旧板房,还有三位留守老人。电脑字库里找不到这个
字,据辞海解释,其意与“汰”相近,而在古徽州方言中,读音为dă,常用于山村地名,其大意为“山腰一小块平地”或“山腰里的村庄”。野猪
在山坳尽头,两条山坞汇合处,称之“野猪坞”或更合适。
小村修竹环翠,一株高大的水杉在村口的竹林里突兀而出,直插云天。棕褐色的两层木板房靠着山脚一字排开,门前的柴垛码得整整齐齐。小溪里的清水潺潺流淌着,一条水渠连着板房间一个小鱼塘。清澈见底的泉水里仅有两条草鱼、两条锦鲤,长二十公分许,它们浮在贴近阳光的水面下,懒洋洋的。这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固定电话,要不是溪边那个“现代理念版”的简易木制厕所,我还真有穿越百年时空的幻觉。
从野猪缘溪下行两三里,进入大连村延伸进来的水泥公路,不远处为汪村镇查山村。从村庄跨过小溪,进入另一山坞。在山坞尽头登高至山顶,再下到山底则是革命老区板桥乡梓溪村,古名梓坞。村庄及附近的山岭上至今仍保存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军及新四军留下的被服厂、野战医院、弹药仓库、粮油仓库、日用品仓库以及会议室、宿营地、红军亭、廊桥等十余处红色遗址。我们所走的这段路也有“红军路”之称。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