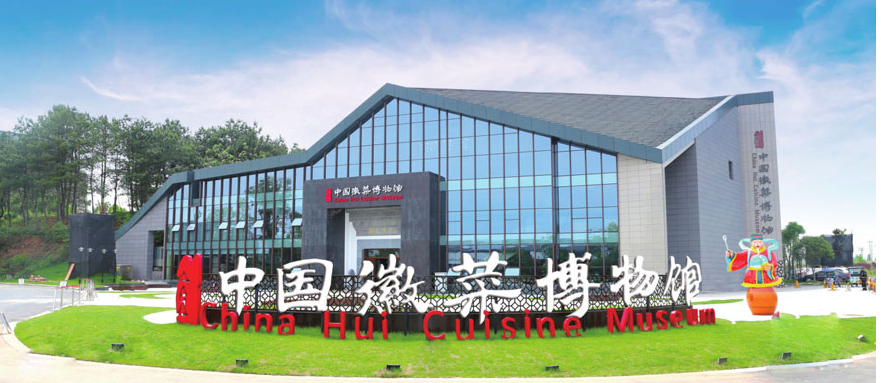杨桃岭古道位于绩溪上庄与旌德江村之间,因路的一头是胡适,另一头是他的发妻江冬秀,而备受瞩目。(全文7800字本期2200字,阅读时间约12分钟)
评价指数精彩指数★★★★☆ 危险指数★☆☆☆☆强度指数★★☆☆☆ 完好指数40%
人的名气大了,与之沾亲带故的一切人和物也就随之珍贵起来,一条路不在于多少人走过,而在于谁曾经走过。横亘在绩溪上庄与旌德江村间的杨桃岭上,有条翻山越岭的古蹬道,它既不是古代官道,也非通衢孔道,更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戍边关隘,充其量是“徽泾官道”的一条支线,村寨间的“乡道”而已。但因路的一头是胡适,“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另一头是他的发妻江冬秀,一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脚女人,这条不长的路也因此备受瞩目。
一
古时,从徽州府城东门出发,经溪头、大谷运、竦坑,越竦岭至绩溪上庄,过旺川,登杨桃岭至旌德江村,是歙县和绩溪县通往旌德西乡的重要通道,目前仅竦岭、杨桃岭上尚存部分石板路面。当年的徽(州)泾(州)官道过翚岭至绩溪长安镇,一路继续北上旌德、泾县,另一路则西行至上庄与该道相连,是绩溪人前往太平县、青阳县及九华山的主要路径。
上庄一带土地平旷,水丰地肥,是古徽州境内少有的千顷良田之地。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这么一处富庶之地,自然文脉深厚、名流辈出,也少不了一掷千金的富商。如今这里村寨棋布,公路交错,我们驱车从屯溪出发,导航加问路,好不容易才在旺川村找到前往杨桃岭的乡村道路。当年缘昆溪而上的古道已被水泥路替代,仅能单车通行的登山公路,经铜罗丘、下舍,可抵达山腰的凤昆村。
从旺川到凤昆,道路缓缓而上,山脊慢慢收拢,大会山在这形成一个喇叭型的山坳。这里有个美丽的名字——凤栖湾。可以想象当年这湾溪水是何等清秀,这条古道是何等繁忙,这片村舍是何等清幽。在这仲春季节,凤溪湾里,清澈湍急的溪水溅起洁白的水花,层层叠叠的梯田里浮起一层金色,粉墙黛瓦间缀着斑斓的色彩:红的是映山红,黄的是油菜花,粉的是桃花,白的是梨花,尤其那李子树,洁白的花瓣簇拥在鲜嫩的叶丛中,绽放着春天的勃勃生机。位于凤栖湾尽头的凤昆村依山而建,几十栋屋舍掩映在青山绿海中,古道穿村而过,如梯如链,这种古意的画卷让人心生几分宁静。只是这静寂的村庄里,绝大部分房屋大门紧闭,甚至门前已长满青草,这些少了鸡鸣狗吠的山村总是让人感到缺了点什么。水泥公路绕过村庄继续上行两三百米,有一停车场,这是一家刚建不久的休闲度假农家乐,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空靈”二字,道路左边是一排木质楼房,门前灯笼高挂,却空无一人。右边还有一栋新建的房子,徽州传统的砖木结构,红砖外墙已砌大半,几名木工正在工棚里开凿榫眼。几眼鱼塘沿溪而建,似乎已很久没人打理了,有的只剩底部一滩水凼,两条草鱼、十几条红鲤鱼在一滩浅水里艰难地游动着,搅起一圈浑浊的泥浆。农家乐左边是昆溪,右边是机耕路。我站在这条曾经的古道上,从历史深处吹来的风悠悠地在我心中漾起一股悠远而苍凉的情绪,那些已经被抛弃被隔离的历史和现实重叠在我眼前,我心中疑问:古村的内核与现代民宿的表象哪一个才是未来的方向?
二
我们沿着村民指点的机耕路向山中行进,不远处就是一座路亭。路亭依山襟路,傍溪而建,但因后来开挖的机耕路从路亭后面辟山而上,导致杨桃岭下来的小溪受阻,山洪冲塌了一面石墙。虽然厚实的石墙还支撑着檩椽瓦片,估计离彻底圮毁将不会太久。
坑坑洼洼上行的机耕路交错密集,通往山中不同方向,绝大部分古道已被机耕路挤占或掩埋。据村民介绍,这些机耕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县里开采石英矿时开挖的,矿点在哪,路就通到哪,从山底一直延伸到山顶。村民说,那些年,整座山都是光秃秃、白花花的,到处是放炮声和石头滚落声,河里鱼虾几乎绝尽,村庄上空弥漫着扬尘。一旦遇上大暴雨,那些挖开的山石泥土就顺着水流奔腾而下,不要说古道,很多溪边的梯田就是这样被埋掉了。现在,古道就剩三段,第一段就在前面不远,另一段在岭头下,还有一段在岭北,去年村里组织了挖掘清理。
果然,前行不久,穿过一片荒芜的梯田后,进入了第一段古道。古道宽约一米,山中就地取材的花岗岩砌成,大部分石块未经雕琢,大大小小的,但路面尚平整,路上的覆土及两边的水竹、灌木有明显的清理痕迹。翠竹山花之间,古道盘绕而上,流线型的石阶路径宛如白链般挂在苍翠之间。过了这段一两百米的古道,又是机耕路,向右转过一道山梁后,见到第二个路亭。据旺川《曹氏宗谱》记载,石亭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由旺川曹氏嫡派祖毓辉出资垒造,供路人休息。这类绩溪境内古道上常见的拱亭,像一座拱桥桥洞,后靠山崖,前临大路,因不需檩椽泥瓦而经久耐用,可几百年不用维修。但如今这已成“危亭”,拱顶上方相互挤兑的转拱石块已下陷,豁口处裂出一道近十公分的口子,仿佛任何一点重力挤压、甚至大喊一声,都有塌落的可能。
路亭里有些阴暗,我屏住气,蹑手蹑脚走进亭内,见石壁上有一佛龛,佛像也不知所踪,佛龛内也未见任何文字。
站在这座风烛残年的石亭前,仰望杨桃岭,我不禁感慨历史的沧桑。据清嘉庆《绩溪县志》记载:“杨桃岭为旌德西乡往来道路,蚕丛荆棘,行者艰焉。旺川曹世科独立修砌石板路十余里,遂成康庄于岭头。”即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旺川人曹世科为让江村嫁来的夫人便于往来娘家,捐资在杨桃岭上铺设了十余里的石板路,而成康庄大道。352年后的1941年,胡适夫人江冬秀回乡省亲,见路面损毁严重,行走艰难,便捐资1000元,耗时两年,重修了杨桃岭古道。1946年4月,胡适致信同乡柯莘麓先生说:“杨桃岭的修理,如款项不敷,望告我们,当早日设法加捐。”
三
离开石亭不远处是现存古道的第二段,一直到杨桃岭岭头。古道穿行在密密匝匝的水竹林中,路边还堆放着清理出来的泥土和竹根,还有砍伐下来的竹子和灌木。看着两边那些依然细密如墙的竹林,可以想象,在村民清理这些之前,这条路应早已掩埋在竹林之下。
古道不长,有点陡,很多路段是沿山坡直线攀升的。路面比先前精致一些,其中一段,一块块石板凿得方方整整的,在整体古道中显得特别显眼,似乎特意作为“样板工程”的。
杨桃岭岭口海拔970米,在两座山峰之间,呈马鞍状,长近百米,宽三四十米,其中一半已劈成机耕路。沿机耕路左行是一处采矿点,高耸的山峰已削为平地,足有三四个足球场大小,地面上凌乱地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石英石,大如屋舍、小似拳头,晶白刺眼,像一块裸露的坟场。当年倾倒在山脊两边的矿渣浮土顺着陡峭的山坡冲下百余米,摧毁了所有的植被,至今尚未恢复。我随手捡了两块晶体饱满的石英石留作纪念,也算记下那个年代、那段峥嵘岁月给这座山岭留下的疼痛和伤害。
立于岭口,旌德西乡一览无余,群峰众峦间,村舍星罗棋布,道路交错纵横,河流蜿蜒崎岖,如在晴朗通透的日子里,不但可见千倾良田上金灿灿的油菜花,在天际间若隐若现的黄山光明顶也可收入眼帘。当年这一带人少田多,歙县“南乡”及绩溪“岭南”山区百姓就是从这条路前往江村挑运粮食的。精明的旺川人在秋收时就到江村收购稻谷,运回旺川存储,并利用旺川丰盈的水流,建成水碓碾成大米后出卖,也使旺川成了徽州地域内一处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集散地,至今村内仍存十多处水碓遗址。
四
也就是在这里,胡适写下了那首《新婚杂诗》(之三):“‘与新妇同至江村,归途在杨桃岭上望江村、庙首诸村,及其北诸山。’重山叠嶂/都似一重重奔涛东向/山脚下几个村乡/一百年来多少兴亡,不堪回想!——更不须回想/想十万万年前,这多少山头,都不过是大海里一些儿微波暗浪!”
胡适第一次过杨桃岭是在1917年8月,时年26岁的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应母亲要求回乡成亲。受到西方教育的胡适既不情愿却又无法抗拒母亲为他订下的这门亲事。此前的1908年,双方家长就已把嫁妆和迎娶物品准备停当,当时的胡适在上海以学业为由硬拖了下来,这次学成回国,他知道再也拖不下去了,只能极力劝阻母亲将婚期推迟至当年年底,并同意双方先见个面。
胡适四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含辛茹苦供他读书,教他做人。当孝道与爱情不能两全时,浸淫中国传统文化的胡适选择了一种殉道的悲壮,他曾对美国留学时结交的红颜知己(或者说是女友)韦莲司谈到未婚妻时说:“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胡适迁就和容忍这桩13岁时就由母亲主导订下的婚事,正是他基于孝道而对母亲的报答,他曾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而另一面,他的内心深处也希望有这样一位母亲满意的发妻来替他尽孝,替他为母亲养老送终,这也是许多“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人对父母尽孝的一种通常渠道。
尽管胡适谈不上对这位未婚妻的感情,但终归是要收下母亲这份礼物的。况且两人订婚13年来一直未曾见面,虽在美国留学期间,江冬秀也给他寄过信件和照片,但毕竟不是真人。对于这次见面,胡适多少有些期待。8月,骄阳似火,胡适从上庄出发,穿村过岭到了江村已是中午,午饭后又匆匆返回上庄。对于这位洋博士而言,来回近三十公里的山路本就疲惫不堪,更失望的是他并未见到这位江村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只是在她那昏暗的闺房里看到一个隔着蚊帐的倩影。这着实让胡适和胡家人很丢面子,很难以接受,并差点闹出退婚的结局。
胡适后来谈起这件事时说,在江家,“我若打轿走了,或搬到客店去歇,那时便僵了”,如在母亲生气时,自己顺势推波,这门亲事也就顺理成章地画上句号,且也不会受到多少道德的谴责。但胡适却以“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来劝慰母亲,用自己的君子仁厚化解了这场风波。胡适第二次过杨桃岭是当年年底。他兑现对母亲的承诺,于1917年12月30日,即胡适26周岁生日(阴历),按旧俗在老家上庄与江冬秀成亲。依徽州婚俗礼仪,一对新人须“三朝回门”(婚后第三天回娘家)认亲。胡适乘轿返程到达杨桃岭头时,不禁感慨万千,世事沧桑巨变,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在历史长河中个人一点得失算不了什么,和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自己这点婚姻上的委屈又能算上什么。他相信时间能够抚平一切伤痕,接受现实比看得见摸不着的理想更切合实际,于是写下了这首与杨桃岭一起载入史册的《新婚杂诗》(之三)。
五
岭口右边的山峰是杨桃岭的主峰,海拔1200多米。过岭口,机耕路往江村方面延伸一二十米后再次与古道分离,这段古道也因此保留了下来。和岭南一样,也是去年才从柴草中清理出来的,不远处就是那处史料上记载石亭。
石亭位于两峰间,块石垒砌,条石门阙,额题“拱天济美”四个大字,款落“明万历十七年(1589)仲冬月绩邑旺川曹世科立”。石亭拱顶夯土,古道穿心而过,远观类似于一条山洞通往山坳南北,故当地人称“世科洞”。石亭内置两排石凳,石墙及拱顶石缝有明显的水泥浆砌痕迹,左边石墙上还嵌有两块大理石新碑,一块刻有:“徽池古道杨桃岭/拱天揽胜客留连/联姻之路多佳偶/伟人故里若比邻/注:胡适夫人与曹世科夫人皆江村江氏/公元2011年春立”。另一块小一点的石碑刻有“2011年4月绩溪旺川村委会重修此亭”。亭内门额上亦有刻字痕迹,只因光线昏暗,无法辨认。据徽州古碑研究专家陈琪抄录,大意是明万历十七年、四十六年(1618)、嘉庆二年(1797)曹世科本人、儿孙、曾孙和玄孙三次重修古道的记录。
“信士”曹世科一家五代奉行行善积德、福有攸归。这次上庄村委会重修古亭,留下诗句,传承两个古村的文脉风水,在山川大地间滋养着文化因子,难能可贵。但对于“徽池古道”之名笔者不敢苟同,不管从地理位置、路径方向,都不能算作是徽州至池州的通道,更非古人固有名称,充其量是绩溪县与太平县、青阳县的一条县道而已。石亭左面的山坡上还有一处古代工事,块石砌成的碉楼墙体还残存一米多高,从碉楼下到石亭南门的巷道也还没完全湮没。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处工事为太平天国年间所建,系绩溪团练抵御太平军之所。在那刀光剑影的年代,不知这“世科洞”上是否也建有城堞设施。
过了石亭就是旌德地界,这段古道虽没清理修葺,但保存尚好,所用路面石板均为青石,且厚实平整,与南面绩溪境内路段判若两个“标段”。这种不同路段不同规格的建筑风格也是徽州古道建设一个特点,古代捐资修路者往往将一条路承包给两个不同的工匠,形成质量竞争态势。双方工匠为赚得口碑,在路径选择、路基开挖时尽量避开软土、水毁路段,铺设路面时,也尽量选取整块、厚实的石材,并开凿平整。有些工匠甚至在路面上凿出记号,将自己的声誉与质量深深地刻印在这些千年不腐的石头上,歙县文昌古道的工匠甚至承诺,在他有生之年,如有一块路面石板晃动,他将用银元去垫平。
古道同样穿行在竹林里,但竹子品种与南面不同,此为燕笋竹。
清刘灏的《广群芳谱•竹谱五•竹笋》记载:“燕笋,钱塘多生,其色紫苞,当燕至时生,故俗谓燕笋。”燕笋竹不像水笋那样又细又密,也不像毛竹那样高挑粗壮,在徽州很常见。和其它竹笋相比,其笋少了些许涩味,多了一份清甜,因此常被移栽至农家庭院或菜园里栽种。因这段山地比较平缓,且古道又高出地面十几公分,虽同在竹林当中,但并未被山土竹根侵蚀,至今保存完好。只是这些年少有行人,且常年阴凉潮湿,路面几乎被苔草包裹。苔痕青绿,修竹玉立,行走其间,宛如画中,别有一番意蕴。
六
这段古道并不长,仅几百米,其余的已被机耕路挤占殆尽,直至山脚。山脚的江村是一个和上庄一样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古村落。江冬秀故居为清代建筑,虽早已易主,且毁坏严重,但主体尚在,即房屋后进,也就是江冬秀当年躲在里面拒见胡适的那间闺房还在。在我以前印象中,江冬秀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一位拿起菜刀斩断胡适移情别恋的农村妇女。而现实中的江冬秀出身仕官之家,读了几年私塾,初通文字。江冬秀一生喜欢打麻将,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著作,一部不落,麻将的斗争睿智和武侠的刚强侠义也正是江冬秀的突出个性表现。
(江冬秀,图片来自网络)
我未见过有文字记载,江冬秀当年拒见胡适时内心真正的想法,但可想象,拒见一位等待了13年的洋博士未婚夫,就不是一般女人具备的定力。江冬秀身上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女侠气魄:在北大时,梁宗岱教授与发妻离婚,她知晓后不但破口大骂,还亲自到法庭为其发妻辩护;她不齿于胡适的“不锈钢哥们”徐志摩抛弃原配去娶陆小曼,并坚决阻止胡适前往证婚;在纽约时,面对爬上五楼窗户的盗贼,她大气凛然地拉开大门,一个“GO”字竟将盗贼“请出”家门,这是她会说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英文单词之一;在胡适与曹诚英有染,且要与她离婚时,她扯着两个儿子,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声称“先杀儿子再杀自己”,竟一刀斩断胡适的孽情。江冬秀烧得一手好菜,家里来了客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徽菜大餐,给足胡适面子;胡适家人的生活困难她总是尽其所能主动慷慨解囊;抗战时期,她一路逃难保命,却还独自带上胡适的七十多箱书籍。
她看透官场的尔虞我诈,劝胡适只做学问别做官。胡适在给江冬秀的信中曾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胡适出任美国大使后,国内曾掀起一阵反胡风潮,她建议胡适借病辞职,并出面请胡适好友张慰慈斡旋,及时化解了危机。江冬秀也不允许自己儿子去做官,她曾对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可惜儿子没听进她的话,官没做成,最后却是一根冰冷的绳子结束了年仅36岁的生命,还落了个“右派分子畏罪自杀”的恶名。
胡适在重修祖坟时,在碑文上写到:“两世先莹/于今始就/谁成其功/吾妇冬秀”。可见胡适对妻子的敬爱之情。
(韦莲司,图片来自网络)
在胡适去世后,江冬秀整理他的文献资料时,特请远在美国的韦莲司写一份自己的小传放进去。韦莲司是胡适在美国时,与之有着一段超越婚姻的爱情,且是为胡适终身未嫁的女人。能主动让自己的情敌写出自传给自己的男人留下一个完整人生,这是何等胸怀!江冬秀一生行善积德、仗义行侠,果断睿智,她把那个年代的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发挥得淋漓尽致,被载入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如果说胡适一生为国事忙,为家事忙,为情事忙,江冬秀的一生则为胡适一个人忙,她不愧天,不愧地,不愧家人,仿佛一位稳坐太师椅的女侠,一生经营着一个男人,一生捍卫着一个男人。
(胡适与江冬秀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七
在这条古道上,还有一处不得不去的地方,即上庄至旺川的古道、如今锦屏山公路边的一座坟墓。这是另一位因胡适而痴情一生的“江南才女”——“曹诚英先生之墓”,也就是胡适所说的那位“远房表妹”。
曹诚英,别字佩声,乳名行娟,1902年出生在绩溪旺川一富商之家,小胡适11岁,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5岁即上私塾,自小偏爱文学,尤爱诗词。1917年胡适回乡举行婚礼,她作为伴娘而与胡适邂逅,后常与胡适通信,也不时作些小诗请胡适评阅,两人互有好感。曹诚英16岁(1918年)那年,由其母亲作主许配给附近宅坦村的富家子弟胡冠英,婚后不久,她即前往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后因其夫纳妾等缘故,于1923年春天,结束了这段父母包办的婚姻。当年4月,胡适因病到杭州西湖畔的烟霞洞休养,与正在此读书的曹诚英重逢,在曹诚英刚脱离婚姻牢笼的当口,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并有了“爱情结晶”。后因江冬秀以死相逼,这段恋情才无果而终。
曹诚英堕胎后,于1925年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先后就读于东南大学农科、中央大学农学院,后留校任教。1934年在胡适推荐及其哥哥帮助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留学,获遗传育种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复旦大学、沈阳农学院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也是最早的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曹诚英1958年退休,1969年回到故乡绩溪,1973年病逝于上海,终身未再嫁。曹诚英事业上的成就并未冲淡她对胡适一生相思的孤独,他们在杭州烟霞洞三个月的浪漫时光像一束微弱的烛光,照耀着她苍凉的一生。在胡适心中,这段恋情也同样刻骨铭心,他在《秘魔崖月夜》中写到:“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在《暂时的安慰》中又写到:“山寺的晚钟,秘魔崖的狗叫,惊醒了我暂时的迷梦。是的,暂时的!……静穆的月光,究竟比不上草门里的炉火!暂时的安慰,也究竟解不了明日的烦闷呵!”
(曹诚英,图片来自网络)
他俩一生的情缘在彼此心中从未移去。1949年4月胡适离开大陆前,在上海和曹诚英见了最后一面,从此天各一方。1962年2月,胡适在台湾逝世两个多月后,当曹诚英从同事口中得知此消息时,却是心静如止水。曹诚英一生命途多舛,晚年更是孤独孑立。病重之际,她将一大包与胡适来往的信件、照片、诗歌等资料托付给现代著名作家、湖畔诗人、儿时伙伴、终身好友汪静之,嘱托他说:“我活着,要好好保管;我死了,必须烧掉”。1973年1月18日曹诚英因肺癌逝世,这些伴随她一生的相思也化作一缕青烟随她去了天堂。
(曹诚英,图片来自网络)
斯人已逝,只留下这段持续半个世纪似断非断的恋情,引人长叹。按其遗嘱,她的家人将她葬在去上庄的必经之路旁,她要在这里等待着她的“穈哥”(胡适小名“嗣穈”)魂兮归来,来世再续前缘。江冬秀用生命捍卫婚姻。当然婚姻不等于幸福,也不等于不幸福,搭火过日子,习惯就好,习惯了就有了幸福感。曹诚英、韦莲司却为一个男人用自己一生去坚守一段感情,谱写了一段令人泪目、超越婚姻的经典爱情。当然这种爱情大部分时候是以悲剧结束的。世间的经典几乎都是悲剧,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外国罗密欧和朱丽叶,等等,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可遇而不可求。
八
从杨桃岭返回旺川时,一场倾盆大雨如期而至。那条因采矿而毁损大半的古道和胡适在这里留下的一生情缘在我脑中始终挥之不去。我突然想起在上庄听到的一个故事:说胡适在外声名显赫,但并未给当地乡亲带来物质实惠,村中另一位在上海经商的上庄人胡卓林却让很多村人跟着发了财,于是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宁要一个胡卓林,不要十个胡适之。
可时间还没过去一个世纪,还有谁知道胡卓林呢?
就像杨桃岭上那条机耕路和古道,前者仅是历史长河中一个轰轰烈烈的逗号而已,而后者虽已风烛残年,但深入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却永远不会衰老,不会消失。(全文结束)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