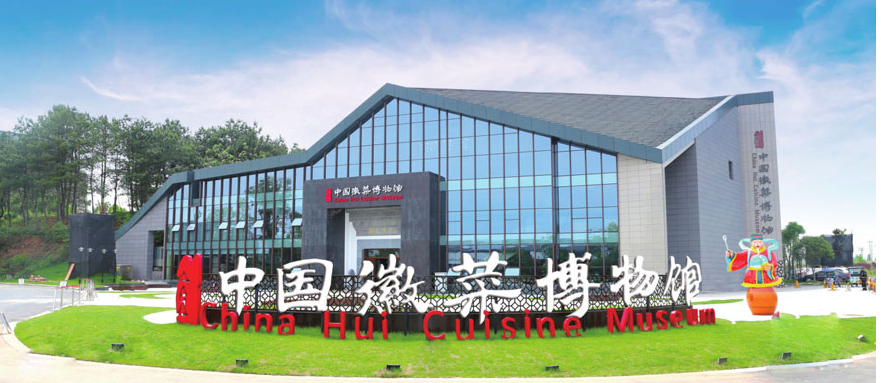竦岭古道连接歙县溪头镇竦坑村与绩溪县上庄镇。古时,上庄人前往沪苏杭,先要翻过竦岭,经大谷运、汪满田、溪头,到达徽州府,再走新安江水路,出徽州,进沪杭。(全文2900字,阅读需10分钟)
古道评价指数精彩指数★★☆☆☆ 危险指数★☆☆☆☆强度指数★★☆☆☆ 完好指数40%
竦岭古道连接歙县溪头镇竦坑村与绩溪县上庄镇。
我是今年走过杨桃岭后,才决定走这条古道的。它们同为一条古道残存下来的两小段,前者在上庄以北,连接旌德江村,后者居南,通达古城歙县。如果说杨桃岭古道是胡适的“姻缘之路”,竦岭则是上庄人走出大山的生存之路,求学之路,经商之路。古时,上庄人前往沪苏杭,先要翻过竦岭,经大谷运、汪满田、溪头,到达徽州府,再走新安江水路,出徽州,进沪杭。
在歙县的地域方位中,竦岭属“东乡”范畴(实际位置在正北偏西方向),古时,出城郭“东门”,所达之处皆为“东乡”。尽管歙县的“东南西北乡”方位与实际地理位置相差甚远,但作为地域名称,一直沿袭至今,且已习惯成自然,就连位于歙县北面的高速公路出口竟也叫“歙县东”。我们从屯溪出发,在“歙县东”出口后,进入溪头镇的乡道。在群山皱褶间,汽车不知跨过多少条河,爬过多少道岭,绕过多少道弯,行程一个多小时,才在峡谷尽头,找到目的地竦坑村。不知当地俗语里所说的“里一扭、外一扭,竦坑螺丝多个扭”,是否就指这些绕得让人头晕的山道。
在徽州,许多村庄是以地形地貌命名的,一个“竦”字加一个“坑”字,足以说明竦坑所在的地势环境——崇山峻岭一洼地。当我驻车村头“广场”时,眼前这片群山拱护下的田园村舍,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或许来自“左语右文”公众号的江老师,相似的童年,相似的山村,相似的瘠土,相似的“跳农门”之路。他从这里走出大山的路,和我那远在“南乡”的路一样,曲曲折折细又长。唯一不同的是,当年这个“大路边”的“岭脚村”,有着更多优越感,据说,古时周边村庄都愿把女儿嫁到竦坑来,究其缘由,竟是竦坑“一有观音忏,二有十月半,三有挑米好撑担”。以前歙县“东乡”人去绩溪、旌德买米,竦坑是必经之地,有亲眷在竦坑,来往绩溪旌德,就可省去了打尖住夜的开支。
竦坑村民以江姓为主,属徽州典型的聚族而居村落,但村庄历史并不长,至今才四百多年。相传,明朝时期,竦坑江姓始祖济元公去绩溪上庄,途经竦坑时,烧了一堆火,热了热随身携带的干粮。次日返程,济元公发现火堆依然余烟缭绕,故以断定此乃风水宝地,随后举家迁居于此,至今已三十余世。徽州村落选址故事千奇百怪,由一堆火诞生的村庄并不多见,何况这种“不利于森林防火”的方式。但这一传说起码可证明一点,竦岭古道在竦坑江姓拓荒成村前就已存在,且是歙县“东乡”至绩溪旌德的一条交通要道。
竦坑村沿竦河两边而建,粉墙黛瓦,临路傍溪,小桥流水。我每次走古道,经过这些“岭脚村”时,都会走进村庄街巷,从那些宽阔的门阙里窥探昔日店肆林立的遗迹,从那些长满青苔杂草的路面石缝间,感受那股来自远古的气味。然而,在竦坑村,几乎每家门口都站着一条龇牙咧嘴的土狗,且未拴绳子,纵使我们手中拿有登山杖,也无法阻止它们的狂吠和追击,让我怎么也感受不到,这个田园牧歌式的徽州山村里,这样的鸡鸣狗吠有何诗意。
也许,农村生活本来就没有诗意。所谓的诗意,只不过是那些文人骚客的臆想罢了,真正像雪庄和尚那样放下一切功名利禄者,是少之又少的。大部分人偶尔去农村走走,也不过是释放一点内心的污浊和压抑而已,就像我们驾车几十公里,就为走一段荒废的古道一样。
走古道从竦坑到上庄近七公里,其中竦坑村到竦岭脚段约三公里,当年缘溪而入的古道,已被砂石机耕路覆盖,如果不是正在开挖的“竦上公路”阻挡,汽车一直可以开到岭脚下。
当然,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走路的。
在这段机耕路上,陆陆续续还有几个小村庄,有的一两户,有的十几户,不知叫什么村。按我们习惯,每到一个村,哪怕几户人家,都会拍张门牌号,留下记录。然而每家门口的狗,无一例外地把我们拒之门外,甚至追出一两百米。在我所走过的村庄中,唯有2003年在云南怒江,那些星星点点洒落在高黎贡山腹地的农户,他们家养的狗可以和这个竦岭下的村庄相比。但毕竟那是在异域,和中缅边境的少数民族同胞相比,我们的“人种”还是有些差异的,群狗抵御我们这些“外侵者”,尚可理解。但在徽州境内,这些狗还对我们这么“见外”,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大概是这条当年人来客往的“大路”沉寂得太久,狗已不适应陌生人了。
从竦岭脚开始登高时,我们才见到真正的古道。
古道路面宽约一米,就地取材的花岗岩铺砌,石阶也没凿得那么平整,充其量是古代的“乡道”而已。古道左边是梯田,右边靠山,路边柴草已清理过,部分路面石板已有塌陷歪斜,但行走无碍。
古道不陡,岭头不高,海拔不足500米,和想象中高耸入云的“竦岭”相去甚远。这也是徽州古道的巧妙之处,它的选址不仅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路径,跨越的山岭也是群峰最低处。在竦坑周边的千米高山大岭间,竦岭就像一个门阙,连接着绩溪上庄和徽州府城。
从岭脚到岭头,不到二十分钟脚程。现在,岭头已无任何建筑,仅有几个供行人憩坐的石头柱础。这几个凿得方方正正的柱础,应该是从哪个路亭的废墟上搬来的,但我们找遍岭口内外,也没找到任何路亭遗址,更别说石碑等文字记录了。看来这条古道的肇建史料,只有从当地老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去寻找一鳞半爪的记忆了。
跨过岭头不远,就可看见上庄。大会山下,良田万顷,交通阡陌,村舍连连。在那片沃土上,上庄人曾创造了畅销苏杭的“时雨茶”,也创造了晚清时期“中华三大奇药之一”的“五胆八宝墨”,胡开文的《地球墨》就是从这里走向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
此刻,站在竦岭之巅,我们仿佛看到了胡传、胡适父子俩从山下走来,跨过竦岭,走出徽州,走向救国之路。他们一个身处千疮百孔的晚清,一个置身内忧外患的民国,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性的宿命,他们为民族奔波一生,为国家效力一世,却都在异乡台湾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120年前,清政府割让台湾后,胡传虽乘最后一支内渡船队离开宝岛,病逝厦门,但他的热血丹心在离台那一刻就已死去。一九六二年,七十二岁的胡适在台湾去世时,他灵魂又何曾没有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呢?他是忘不了山中这一缕淡淡的兰花香的。
沧海桑田,时势更迭,如今唯有这条寥落在这青山绿水间的青石古道上,还拓印着那些厚重的脚印,闪烁着那些匆匆的身影。
下山的路略平缓些,部分路面由凿磨平整的青石垒砌,不管是路面宽度,还是石阶精致度,均高于南坡,其中两处精美的弧线型弯道,还成了古道的标志。只是现在少有行人,路面两端,已被山土、柴草侵占大半,仅剩当中窄窄一线,供当地乡民上山劳作时行走,还有我们这些磨脚出汗的“驴友”。
走出林荫,临近山底,有一路亭,砖瓦结构,古道穿心而过,两端拱门均题额“半岭亭”三字。这是竦岭古道上唯一残存的建筑物。走进亭内,石灰墙面斑驳脱落,垃圾遍地,还有不少牛屎。所幸左墙题款尚存,以此获知古亭身世:“半岭亭于壹玖肆柒年贰月由上川老胡开文广户氏兴建。几经风雨,年久失修。今由香港、深圳华生印刷厂程振华先生捐资重建。谨誌。贰零零肆年捌月立。”
题款边上还有一首打油诗。当然也不缺“到此一游”之类天马神空的涂鸦。
半岭亭下是一座微型水库,水库之下是一条刚修建不久的公路,公路不远处就是胡适的老家上庄了。水库以下的古道也自然消失在这些现代建筑之下。
在现代建筑面前,这些已失去主要交通功能的青石古道,就像那些从明清穿越到现代的老朽一样,自然不再有人待见它。不知那条竦坑至上庄的在建公路,是否会避开这段不足三公里的古道?给竦坑、上庄人留下一段记忆!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一日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