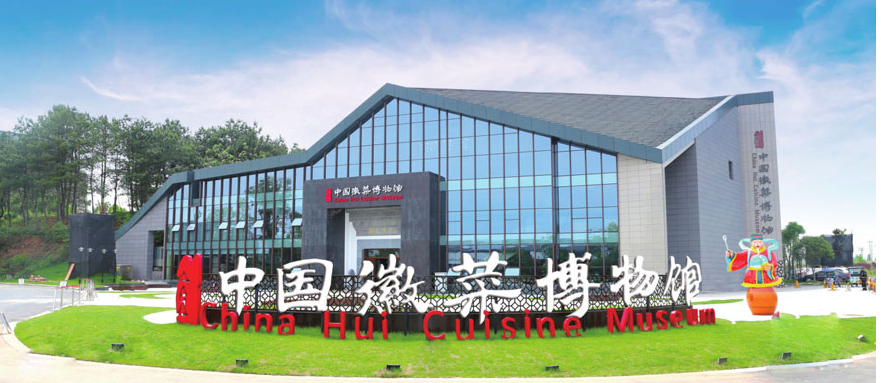连岭古道为“休龙古道”中段,古时自休宁海阳镇起,经屯溪、榆村、石门,越啸天龙,至淳安县汾口镇龙山街(现龙山村)。现存古道起于歙县石门乡,至淳安浪川乡连岭脚村狮古山组,全程号称“六十里”,即“上二十,横二十,下二十”。(全文7000字)
评价指数精彩指数★★★★☆ 危险指数★★☆☆☆强度指数★★★★★ 完好指数70%
古时,两脚走天下,山路弯弯,天高路远,“六十里连岭”多少有些夸张,但即便打个折,单程也有二十多公里,往返四五十公里,确实不是我们这些成天坐办公室者可承受的。于是先短后长,先易后难,2017年深秋,先走“横二十”,路面平缓,秋色绚丽;2019年9月,从石门出发,走“上二十”,林木荫蔽,古道幽深;2019年10月,挑战极限,全程往返,顺便检测一下我这运行了半个世纪的老骨架。
一
《歙县志》载:“三国贺齐出守新都,凿连岭,以通江浙”。据史料记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孙权派部将贺齐出兵剿灭金奇、毛甘、陈仆等领导的歙黟山越人,建新都郡,辖现黄山市(不含黄山区)及石台县、婺源县、淳安县、建德市的大部分地域,郡治始新县(今浙江淳安县千岛湖西北、威坪镇附近)。因治于郡域东部,为便往来,贺齐组织开凿连岭山道,以通东西。此后,郡治先后设于海宁(现休宁古城岩一带)、黟县,直至隋大业三年(607),新安郡迁歙县至今,连岭古道一直为古徽州(新都郡、新安郡)东西交通大动脉,是徽州有史料记载以来开凿最早的古道,比隋大业十二年(614)汪华主持开凿的箬岭古道整整早了四百年。关于连岭古道的来历,还有两种说法,一为两地高僧托钵化缘所建,另则与朱元璋及其军师朱升有关。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号枫林先生,休宁回溪人,至正元年(1341),登乡贡进士,四年后,授池州路学正,两年后方才赴任,不久便弃官回乡,后避隐歙县石门开馆讲学。元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朱元璋久攻婺源不克,听闻徽人朱升文韬武略,便寻访到休宁回溪,朱升却留下“杀降不祥,唯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的锦囊妙计后避而不见。朱元璋依计攻克婺源城后,决意效仿刘备三顾茅庐,招贤朱升。当他察明朱升在石门讲学,便佯装成商队,自严州府(现建德市)出发,过连岭,至石门,来到朱升教馆前,请其出山辅佐。时值元人暴政,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二朱相谈甚欢,朱升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思想。朱元璋当即遣礼相聘,拜为中顺大夫。此后朱升一路辅佐朱元璋,创建大明江山,官拜翰林学士,直至洪武二年(1369)告老退隐,而得以善终。相传连岭古道就是这一时期朱元璋派兵修建的,如今古道上还有“宝剑泉”“绝檵木”“送驾岭”等与朱元璋有关的景观或地名。岁月漫长,古道悠悠。只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交通的飞速发展,这条曾经的徽州东西大通道,已逐渐淡出视野,且部分路段毁损后未得到及时修复。值得欣慰的是,前阵子得知,连岭古道已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保护性开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下,作为“文物”先保护起来,是为上策。
二
清晨六点,从屯溪驱车出发,穿过石门村口那块刻有“朱升讲学地”石碑后,汽车沿着清澈的小溪,继续向山坞深处前行。路边山崖断面上黝黑的岩石,见证了古道曾经的路径。古道所在山坞土名芝麻坞,至尽头可前往歙县狮石乡及淳安中洲镇,古时,从这里至遂安,是继仰山、白际岭后的第三条古道,据说在狮石境内的“三善亭”与前者的“一善亭”、“二善亭”同出一辙,其形制相同,题额也出自一人之手。距
石门村约五里处,为现存古道起点,也是前往石门林场的必经之路。古道宽约两米,石阶位于路面中央,古时应是人畜并行的“双车道”。这样的路面设置,虽未精雕细琢,但应是规格较高的官道。此处土名婆岭山。古时对婆婆都没啥好印象,这段古道亦然,开始进入,即沿陡坡直线登高,多少有些不适。古道两边是人工种植的杉木,去冬刚有间伐,老桩上已长出新芽。砍下的树木还未去枝,有的横亘在路面上,钻或跨才能通过。刚登高上行不久,在爬过一根横跨路面的杉木时,我的小腿就被一股断枝划了一道口子。当然隔着裤子的,创口不大,和那些因树木滑行下山,而冲塌的路面相比,几乎可以忽略。给今天登山增加难度系数的,还有天气,虽然预报阴有小雨,但山中昨晚已下过雨,匍匐在石阶上的青苔,以及数百年留下的沉垢,一经雨水浸泡,仿佛敷上一层地膜,十分湿滑。我们只能踩在石阶两边或缝隙的杂草上,不足半小时,鞋子已完全湿透,发出咕叽咕叽的摩擦声。
登高约四十分钟,到达第一层山脊,土名前山。这是一个丁字路口,沿路口往北翻过一座山,有个叫古祝的山村,属歙县绍濂乡管辖。首次走连岭时,遇到两位采箬叶老人,我试图了解一些关于这条路的史料,但老人的方言除“古祝”二字外,其它一句都听不懂。路口是几块梯地,种有枫树和茶树。茶树是以前种的,长长短短的,间或还有几股灌木突兀而出,显得有些凌乱,似乎已有几年没人打理了。枫树应是二十年前退耕还林时种的,碗口粗,如天气晴好,蓝天白云下,这片火红的枫林该是一片亮丽的风景。遗憾的是,近期雨雾漫漶,红枫已黯然失色,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凋落了。它们走过春光,跨过酷暑,如今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凋零而去,真让人有些不舍。古道后面的梯地里,有一处建筑遗址,石基尚存,约30平米,预计是以前的路亭,亦或是客栈。古时歙县西部前往睦州,这该是必经之地,到了这里,停下沉重的脚步,回眸一看妻儿老小,再歇口气,喝口水,然后毅然决然地走向那迷茫的远方。此处也是这片山林的分界线,其下是人工种植的杉树,整齐,峻拔。其上是天然灌木,稠密,杂碎,如今烧柴火的人少了,这片林地也越长越高,越长越密。这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庄子携弟子出游,途中,看见有人伐木,成才的都被伐去,留下歪瓜裂枣的,庄子对弟子说,还是无才好吧,弟子皆以为然。晚上,庄子一行住店,店主杀鹅款待,但两只鹅杀哪一只呢,最终还是决定杀那只叫声不好听的,庄子又说,还是有才好吧。弟子茫然,问庄子,到底是有才好,还是无才好呢?庄子说,介于有才和无才之间最好。
三
过前山,经一段平缓山脊,进入第二层山峰的登高路段,也是另外一条山坞的汇合点。
或许是两条山坞的水汽在这里汇合的缘故,刚才一览无余的山峦,此刻全部躲进了青灰的浓雾中,能见度不足十米。浓雾中还裹挟着细密的雨丝,湿漉漉的,似乎随手一抓都能挤出水来。茫茫的雨雾中,行走在这九曲环绕的Z字型登山盘道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机械地往前走着,就像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一样。看不见远方的风景,走路成了唯一目标,也就不再觉得那么累了。很多时候,人活得累是因看到太多的风景,激发太多的欲望,或是看得太清晰,看得太透,而失去了前行的动力。什么都看不见,也就不再去想那么多,心静了,寡淡的生活自然有了味道。在汗水和雨水的交织中,我们抵达狮石公路,即石门林场冷水洼林管站。时间正好八点,行程四公里,耗时一小时二十分。狮石公路起于长陔岭头,前往歙县狮石乡,与淳安县中洲镇、休宁县白际乡相连,全程28.5公里,2006年建成通车,标志着安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乡镇成为历史。公路蜿蜒在海拔700-1000米的群山褶皱间,外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山坡峭壁,没有护栏,没有行道树,后壁劈山而立,裸露的岩石摇摇欲坠,整条公路仿佛绝壁上凿出的一条“栈道”。且因路基沉降,霜雪冰冻,山洪冲击,塌方落石,路面早已面目全非,我首次走连岭返程时,天已黑尽,即使开着大灯,能见度也不足十米,现在想来仍心有余悸。如今公路重新硬化,平整的水泥路面已成“浙皖天路”最精美路段。
走连岭古道次数多了,和护林员已混了个脸熟,每次到这都要坐下喝口水。而今天刚一坐下,就感到肚子突然上下倒腾,呼之欲出一般。在我身体的零部件中,最不争气就这肠胃,冷了热了,都可能罢工抗议,或许今天吃得太早,餐后不久即开始急速行走,再则,这冷水洼的风,即使炎炎烈日,也是冷飕飕的,刚才我一路挥汗登高至此,被这风一吹,“内部矛盾”自然提前爆发。人有三急,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是免不了的,当年郁达夫与林语堂到昱岭关时,也在关门边上“撤了一泡溺”,以作过关纪念。行走山野,我也顾不得斯文,找个隐蔽处,宽衣解带,就地解决。估计来年春天,这千米之巅的千年古道边,定会催生一丛突兀而出的浓密柴草。卸下体内包袱,喝口热水,肚子顿感通泰,继续进入古道前行。上行不远,见一房屋遗址,一石横卧路边,形似匐地休息的牯牛,不知这块石头有没有什么讲究。石边有一古树,高近十米,两股主干并立,直径六七十公分,且树干已枯烂近半。此树虽貌不扬,却是国家一级保护树种,树龄已近千年。这是去年网上看到的消息,树名已记不清了,且如今叶落枝枯,树老皮厚,苔草包裹,“花伴侣”也无法识别。实际上,这里才是真正的“冷水洼”,因附近有泉水常年不枯不溢而得名。此处坐北向南,避风朝阳,原为林管站驻地,公路修通后,才搬迁至路边的“风口”上。交通是方便了,却只剩下常年寒风呼啸的“冷”。
四
原林管站两间平房因常年无人居住,已梁塌瓦落,周边坡地抛荒已久。古道边还有一处古建筑遗址,其占地面积与林管站相近,圮塌时间应在百年以上。相传,古时曾有人逃荒至此,见此地阳光充裕,土壤肥沃,水源不断,便在此安家落户,故又名逃荒岭。连岭古道连接徽(州)睦(州)两州,人来客往频繁,少不了客旅食宿、畜禽草料需求,逃荒岭便成了一间客栈,生意颇为兴隆。但久而久之,客栈主人却见义忘利,把当年逃荒果腹的日子忘得一干二净,从起初的坑蒙拐骗演变到后来的谋财害命,最后走上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不归路。也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牢牢地钉在六十里连岭的耻辱柱上。
离开逃荒岭不久,即到达古道最高点,进入“横二十”路段。在山巅逶迤蛇形的古道,一会儿在峰尖的南面,一会儿绕到北面,就像奔泄的涧水,若隐若现在茫茫丛林中。两千年来的朝代更迭兴废,从这里一路走来,古拙,苍劲,幽深,一种喧嚣之后的落寞弥漫着整条古道:磨砺得失去棱角的青石板已被岁月的风尘染成黑褐色;那些熬过数百年的朽木,虽已叶落枝断,皮脱肉露,却仍然扎根在岩石缝隙中,像一尊尊雕塑,矗立在古老的森林里;碗口粗的猕猴桃藤又黑又糙,绿苔缠绕,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枝头还缀满一串串咖啡色的果子。我第一次走连岭,已是初冬,天蓝蓝,白云朵朵,远方腊染层林,身边野果累累,山楂、木棉、石楠,还有铁红的枫叶,黄橙橙的金钱松,都在绽放着一年中最后的精彩。而此刻走在这海拔1300米的山脊线上,风和雾带来的却是凉丝丝的寒意,视野所及,茫茫一片。
不觉中路程已过半,我们就地在一处古亭遗址前暂歇。遗址名“乌门洞”,俗称“无门洞”,为徽睦界亭,现皖浙省界,古有“一脚跨两省,鸡鸣醒三县”(歙县、淳安、遂安)之称。乌门洞原为“穿心”亭,拱形门洞,相传始建于唐代,后屡修屡废,屡废屡修,如今仅剩这些倒落在地的巨大块石,横七竖八的。过乌门洞,为一处平坦开阔地带,传为朱元璋部将胡大海的养马放牧之地,古称“百马场”,现名“观音亭尖”。古道在这里绕了270度大弯,其正面又是一处路亭遗址,规模不大,约十几平米,亭内柴草丛生,无法涉足。亭前有一铁皮牌子,记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役概况,几年前才立的,现已斑驳不清。据史料记载,1934年9月24日下午至深夜,为保红七团主力安全翻越大连岭,后续掩护部队在距连岭岭脚两公里的送驾岭上,迎战围追而来的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九师和补充第一旅五个团的兵力。按军团长寻淮洲部署,红军巧妙地利用敌补充一旅错把“浪川鲍家”当成“双源鲍家”而迟到的战机,同步佯攻围追而来的敌军双方,导演了一场敌军互打的好戏,亡敌一百五六十人,使得五千多红军战士成功甩掉一万三千人的国民党军队,史称“送驾岭之战”。原来在观音尖下,还有炮台、战壕等工事,现已了无痕迹。
五
当年红军冲破敌人围追堵截,从这里走向为民族独立而抗争的新战场。而今天在这里“围堵”我们的却是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软体动物(蚂蟥)。照理说,时值深秋,这千米高山,即使大白天,温度也仅十几度,这些小生物早该钻进泥土等待明年春风送暖了。而今年或是持续干旱缘故,天还没凉下来,这雨后的腐叶却成了它们的掩体,行人一旦经过,便会弹跳而上,为过冬前再汲收一顿丰盛大餐。出发前,我就将裤脚绑在袜子里,并带上护袖、手套,没想到还是被“临幸”了。难道这小东西有缩身术,能从袜子缝隙里钻进去不成?所幸没有遭遇那些还未储备足够脂肪而忘了冬眠的爬行动物。有“追兵”的行走速度是最快的,我们一路疾行约8公里,从冷水洼穿越半个连岭抵达最高点“啸天龙”,竟不到两小时。一听“啸天龙”这个地名,就是有故事的。相传,西晋时期“中原南渡”后,皖南人口骤增,新安各县百姓往来频繁,然连岭柴草没膝,行走艰难,故有两地高僧托钵化缘,筹资修建此道。山道连通之日,高僧在此不期而遇,喜极而拥,长啸一声,化龙而去。在高僧羽化处,如今是一座“思红亭”,内有一石碑,寻淮州、粟裕、乐少华、刘英……北上抗日红七军团将士的英名永远镌刻在这连岭之巅。
啸天龙也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当年朱元璋在此留下的传说就足以写满几页纸。山脊南面下行十多米,有一甘泉,常年不枯不溢,相传朱元璋领兵至此,口渴难耐,于是一剑插地,顿时泉涌而出,故名“宝剑泉”。据说,为防止泉水被敌军利用,朱元璋还立下“此泉吾开,敌众勿来”的口谕,后人只有轻手蹑脚走进泉眼,才有清水流出。故事里的事,可信,也可不信,但这千米之巅,一汪清泉,四季喷涌,本身就是奇迹。遗憾的是我几次前往,都未能找到这一眼圣水。啸天龙下行约2公里处,还有一棵大枫树,上粗下细,据说当年朱元璋随手折了一股枫树枝,倒插在土里,后来竟长成大树。几百年来,枫树一直枝繁叶茂,夏日葱茏如伞,秋天霜叶似火,可惜也未躲过六十多年前那场“大炼钢铁”,数百年的古树成了一堆柴火,化作一缕青烟,追随它的主人去了。
六
在啸天龙休息十分钟后,我们继续走最后一段路程——“下二十”。这段坡道上缓下陡,中点为“箬帽尖”,即“十里亭”。上段俗称“十八肩”,据说古时挑担上山者在“十里亭”歇脚后,换肩十八次即可到达啸天龙。如今这段地处山林腹地的古道,多处路面被山洪冲塌,且柴草簇拥,偶有枯木阻路,是整条古道中路况最差的一段。下段依山折叠而上,峭如天梯,类似“十八弯”,为连岭古道精华所在。前些年,山脚的狮古山村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对古道进行了清理维护,复建了“三里亭”、“五里亭”,还在村口建起“狮古山红军广场”、烈士陵园等红色旅游设施。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们经过近四小时的上坡路、横排路,这要连续八九公里的下坡,腿已有些不听使唤了。当然这样长距离的下坡,即使汽车的刹车鼓也会发红了,何况这尊凡身肉体,更何况是这雨后湿滑的石阶。我们几人几乎都摔了跤,个个一身泥,最惨的一位老兄手指根部还撕开了两道口子。俗话说“看到屋走到哭”,不知走过几条湾,跨过几道矼,在古道上迂回盘绕近两小时,终于在中午十二点抵达山脚的狮古山村——红色连岭的桥头堡。
狮古山村地处淳安县西南部,古属遂安,1936年6月,中共浙皖特委在此成立,并成功召开第一次特委委员会议,组织领导淳安、遂安、歙县一带革命队伍开展武装斗争,诸多红色革命旧址尚存。但因时间缘故,我们用过便餐,走马观花看了两座古石桥(万年桥、连峰桥),拍了几张古碑照片,便马不停蹄开始返程了。连岭古道“上二十、横二十、下二十”是泛义上的,从狮古山村到啸天龙的“上二十”路段,几乎占总路程的40%。阴雨天气,山谷幽暗,不到六点就已天黑,也就是说我们下午的有效行走时间不足五小时,返程强度将大大高于上午,否则得摸黑下山。在与村民交谈中,也证实了我们的预判,“郎跺脚”便是见证。相传古遂安山区有娶亲背新娘习俗,即新郎上门迎亲,须将新娘背回家,途中可换人转背,但新娘双脚不得落地,否则可悔婚不嫁。据说,古时歙县石门有位石匠,相貌丑陋,自恃力大无比,或是不愿别人“揩油”,决定一人独自背回新娘。娶亲那天,石匠自遂安浪川出发,一路背负至此,面对这些天梯般的石阶,已是精疲力竭,寸步难挪,不得已把新娘放下,稍歇片刻后再继续攀高前行。哪想新娘本就对这婚事不满,这一落地休息,正中其下怀,一溜烟跑回娘家,弄得石匠后悔得直跺脚。“郎跺脚”之名便由此而来。
很多时候,人的潜能是逼出来的。当我弯腰弓背行走在这近五公里的“十八弯”上,粗犷的喘气声如汽车爬坡“轰油门”一样,震荡在直插云霄的盘山磴道上。五十年前的今天,在那个同样位于峡谷尽头、大山环抱的山村里,我来到这个世界,五十年的奔波,五十年的路,今天,我以这种极限行走的仪式来定格这五十个春秋。将来终有一天腿脚不利索,哪里都去不了,甚至牙齿掉了连撮一顿都没滋味的时候,想起今天这一路行程,或许还可慢慢咀嚼一番。返程的路依旧湿滑,六十里连岭依旧雨雾重重,小小的蚂蟥依旧弹跳到身上。我们经箬帽尖,跨啸天龙,过乌门洞,走冷水洼,一路登高穿山,返回到古道起点时,天已完全黑尽。
此刻,我的脚掌、脚趾已磨出多个血泡,像一只跛脚的鸡,一瘸一拐的。(2019年10月)
2021年9月,我再次走连岭古道,从石门出发,“上二十”、“横二十”,抵达啸天龙后,原路返回。与前几次相比,起点至前山约1.5公里路段,已杂草丛生,须用登山杖“打草惊蛇”,才敢行走。其它路段因村民散养黄牛,路面石板毁损严重,泥淖连连,牛屎遍地。路边低矮的灌木,并不浓密的青草,已所剩无几。“思红亭”的栏杆、坐凳也已被毁。据护林员介绍,这十几公里山路上,最多时养了200多头牛,他们原先还在冷水洼老驻地那里种点青菜萝卜的,现在什么都种不了,有时甚至连晾在门口的衣服都会被牛撕碎。
我站在啸天龙那片曾经的高山草甸上,只见山石裸露,枯树嘶鸣,山风呜咽,仿佛一处刚经历过烽火硝烟的战场。我不禁疑问:难道古道起点处那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是闹着玩的吗??
(2017年拍摄的秋色)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