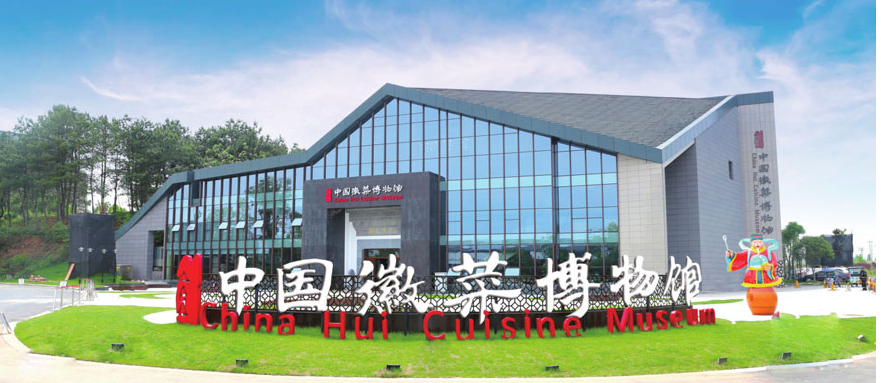歙县“南乡”的“水南”“旱南”是从南源口开始分路的,沿新安江而下为“水南”,沿徽杭古官道至昱岭关为“旱南”,其间一山相隔,多条步道跨山相连,槐棠岭古道是为首条,其后还有大阜至深渡(梨树岭)、七贤至定潭(太岭、婆岭、公岭)、郑坑店至昌溪(光坑岭、朱岗岭)等古道。
槐棠岭古道北起歙县北岸镇呈村降村,翻越槐棠岭,过槐棠村,在漳潭乡漳坑村(现属深渡镇)道分两路,一路至大脉坞村,一路至坑口乡汪龙坑村,全程10-15公里,终点均在新安江畔。古时,新安江南岸的坑口、小洲及其所属诸多村寨,走旱路东进杭州、北上绩溪等地,一般要经过这条古道。(全文4200字)
评价指数精彩指数★★★☆☆ 危险指数★★☆☆☆强度指数★★☆☆☆ 完好指数80%
(古道)
—1—
呈村降是杭瑞、溧宁高速的枢纽,古道入口已被交错纵横的匝道挤占,现在穿过“留村”对面的田埂,穿高速公路涵洞,跨过小溪,走上一座单拱石桥,即进入古道。小溪宽不过2米,石桥小巧,且桥身长满草藤,桥额已无法辨认。过桥不久,古道即沿山体攀高,路面宽约1米,弯道处可达1.5米,青石铺设,凿砌平整,基本保存完好。上行约15分钟,至第一层山脊,古道拐了一个S形弯绕至山脊西面后继续上行。
山脊处有一路亭,一面临山,两面石墙,顶盖鸳鸯瓦。这条古道上,这样的路亭有6-7处,形制相似,此处与岭头两座为原址修复,其他均已梁塌瓦落。再次上行约10分钟,与盘山公路交汇。公路连接槐棠等附近几个高山村落,也覆盖了这段古道。新的,旧的,总是这样在这不知不觉中更替着。
我原以为槐棠村因槐树海棠而来,如今正是花开季节,浓郁的槐花香味和淡雅海棠味调制而成的味道会是什么样的呢?高高的马头墙外,探出几支海棠,绿叶如缎,粉花点点,随风摇曳,也是一幅溢满诗意的乡村画卷。兴许还能顺手摘一捧槐花,晚上回家弄个菜,把春天的芬芳吃进肚里,想想都觉得美妙。然而,我们到达槐棠岭岭头,视野所及是几株华盖如屋的大樟树,树龄均在200年以上。随后,几乎走遍整个村庄,连槐树或是海棠的影子都没见到。
(槐棠村口)
听村民说,这里以前叫“李黄塘”,村民以胡姓为主,为婺源清华胡氏后裔,谱称“清华常侍胡”,即唐昭宗李晔之子胡昌翼的后裔,俗称“李改胡”。
槐棠胡姓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迁入,至今已700余年。“李黄塘”该是当地方言“音译”而来,按其始祖胡姓推测,其初始村名或是“李胡塘”,后来雅化成现名,而与槐树或海棠均无半毛关系。
槐棠村依山而建,有近百栋房子近百栋。和大部分山村一样,如今村中空荡荡的,偶见一两位老人闲坐门前,或是在打理着村边的菜园。一位老人挑着一担春笋经过,看见我们这些陌生面孔,便主动向我们推荐说,村中有堂大房子,共三十六个门阙,前后十八代人才建造完成。
在徽州山村,不乏深宅大院、雕梁画栋,但一栋房子历经十八代人、近400年的雕琢才建造完成,却从未听说过?我们怀着极大的好奇找到这处“豪宅”。严格来说,这是一处建筑群,两条高高的石塝,在并不平坦的山坡上硬是堆出一块约2000平方米的平地,其中塞满各种建筑,包括主楼一栋,左右裙楼,其它辅助建筑近10间。
整个建筑群为一个整体院落,前后石塝形成自然围墙,东面门楼高近10米,其青石门柱、青砖门檐、镂空砖雕,一派大户人家气魄。院内前有石栏,地面铺青石。目前主楼尚存,但已摇摇欲坠。左右裙楼基本坍塌,仅剩门楼或断墙。辅助建筑圮毁近半,门楼上的大部分砖雕已被撬去,部分无法起出的石雕尚存,室内木雕不得而知。从残存的青砖水枧、水管看,当年的建筑工艺可谓精益求精,在徽州境内实属少见。
据村民介绍,楼主人历代在杭州经商,在这块风水宝地上,他的子子孙孙们,房子一栋连一栋续建,雇佣的工匠也一代接着一代干,直至到了第十八代,这处建筑群才算真正完工。从现场看,人去楼空大概是在这十至二十年里,现存主楼等如不维护,归于尘土也就眼前的事。在不久的将来,那高高的门楼里,曾经的荣光也将永远被埋进这阔大的废墟里。
(废弃的石磨)
—2—
说到槐棠,就不得不说山对面的后降(矼)村。
两个村庄同样在这条山谷尽头的半山腰上,槐棠在北,后降居南。尽管后降已是一个准无人村,但这个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却流传着“先有后降、后有大阜北岸”的说法,其当时的兴盛程度远在槐棠之上。
我们走的古道穿过槐棠村,沿山坡下至谷底,跨过一座单拱石桥,即为前往后降的丁字路口。右行为主干道,至漳坑村,左行登高至岭头,即后降村。
岭头距后降村约100多米,古道边一口古井十分显眼。古井位于靠山坡一侧,井台四周铺有青石板,井圈为四方形,由四块厚约10厘米的石板铆接而成,正面镌有“古井重修”四个阳刻大字,落款为“道光元年”。也就是说,1821年是重修古井,其开凿年代已无从考据。
(古井、远处为槐棠村)
我原以为这口井是供路人饮水解渴的,从附近两位采茶村民口中得知,井是后降村的主要水源。
古时这是一眼泉水,上方山坳里还有一眼,相传,这两眼泉水是两只“金鸡”的鸡窝,上为母鸡,下为公鸡。后来槐棠村一户人家把女儿嫁到后降村,并唆使女儿在“公鸡鸡窝”处开凿一眼水井。据说当时开挖不久,就出现了一道闪闪金光,突然一只“金鸡”飞出,飞到了山脚的金山村(即高速公路歙县出口处,古名“金鸡石村”)。
古人语,富贵在源头,后降与槐棠隔空相望,不是你富就是我贵,后降的“金鸡”飞走后,村庄日渐衰败,对面的槐棠自然日益兴旺起来。在高山村落里,水源是极端重要的。尽管后降人认定,槐棠的发达是因破了他们的“风水”,但不管动机和结果如何,出资凿井都是值得敬重的,再说,果真如此,按古时宗法势力,早就把井给填了,何来“古井重修”呢?村庄的兴废本就历史规律,它与环境、生产力、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相关。
今天出现诸多后降这样的无人村,便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产物。我们走进空荡荡的村庄,只见残垣断壁,杂草丛生,一片人类撤离后的衰败景象。返回古井,我再次探头向井下望去,井壁杂草萋萋,黑洞洞的,没有一丝亮光,里面似乎是有水的,又似乎没有,一切仿佛都已被岁月掏空。
当然这井有没有水已无关紧要,即使后降村还有人居住,自来水也已代替这口古井,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3—
从后降再回到谷底的古道,丁字路口边是一座路亭,檩椽已塌,厚厚的石墙依然矗立。亭内长满杂草灌木,隐约可见内壁有一佛龛。佛已不存,佛碑似乎是掉落后又重新架上去的,我本打算进去看看佛碑上的文字,但看着眼前这草木葱茏的样子,想想还是算了。
从丁字路口到漳坑村的峡谷约3公里,缘溪而行的古道比先前略窄,路面石板基本保持原状,杂草较多。据同行者说,他们去年初探这条古道时,已完全被柴草掩埋,行走十分艰难。
好在去年冬天已进行清理,不然这草长莺飞的季节,谁还敢走这路。这段古道上,最显眼的就是桥,短短几里路,竟有四座单拱石桥和一座平板石桥。
平板石桥长近2米、宽约1米,是单独一块青石板搭建的。单拱石桥大小不一,每座拱顶均有题额,仅一座尚可辨认,桥名“五福桥”,落款“乾隆乙巳年██月█”“里人胡█廷造”。
桥建于1785年,也就是说这条古道至少已存在200多年。
古道修建之时,正是徽商鼎盛时期,除来往客旅外,这一带所产农产品通过水路运往杭州的,这是必经之路。而如今公路已通达各村,且这古道两边的水田也荒废已久,谁还来走这条路呢?古道至漳坑村,道分两路,一路翻越瀹坞岭至汪龙坑,1个多小时行程;另一路前行十几分钟即漳潭乡碧溪村,后沿溪涧下行可至新安江边,已有乡村公路通达。其间另有一条古道翻越高溪岭,也可达汪龙坑村。
从这些交错纵横的青石步道看,当年这些山沟里的小村庄还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实际上,每次走进这些偏僻山村,都有一种走入明清徽州的感觉。
进入碧溪村那一刻,我竟想起李白在太平碧山村写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我们在这山中见到的哪一座古村不是“别有天地”呢?但是长期住在这里,能经得起外面世界的诱惑吗?尤其是年轻人。
—4—
走这条古道,大天寺是不得不去的。严格来说,是大天寺遗址,位于大天寺峰巅,海拔824米。古时上大天寺有两条路,均铺有石板,北线从呈村降出发,经高山村,到达山顶寺院;南线走向坑村,也是古时僧侣香客走得最多的一条路。
还有后降、碧溪两村,也有樵道可达,我们是从后降村横穿至大天寺峰腰,沿其古道到达寺院遗址后,再下到碧溪村的。上到大天寺的古道宽1-1.5米,其路面及凿砌工艺均高于槐棠岭古道。古时,到寺院的路都是上山朝觐的香客捐建的,仰山寺、高湖寺、百培寺等古道,均如此,其建造规格都不低。很多时候,信仰的力量是巨大,尽管绝大部分人所谓的信仰或多或少带有功利性,就如丰子恺《佛无灵》文中所说的,是在“和佛做生意”。
但不管怎样,人在佛前,总是极力释放心中之善,收敛内心之恶的。善多了,恶少了,这个社会自然美好了。登高约40分钟,到达大天寺遗址。遗址位于梯状山脊节点,后靠峰,前瞰谷,坐南朝北,视野开阔。整个建筑遗址面积1000多平方米,已长满杂草和竹子,有少量灌木丛,担杵般粗细,原有建筑格局已不明显。遗址北面砌有一石坛,依山就势,其上架有木柱檩椽,鸳鸯瓦,如一座路亭。亭额嵌一木板,用墨汁写有“藏经阁”三字。
(大天寺遗址)
“大天寺”又名“玉岐寺”,分东西两院,曾供有高僧的肉身菩萨,为古时歙县的十大寺院之一,清道光版《歙县志》载:“玉岐寺在长乐下乡大夫山,宋咸淳中建。”
相传朱元璋曾在此修炼,并初显帝王之象,“玉岐寺”之名也因其而来。在附近村庄里,至今还流传着诸多关于朱元璋在大天寺的传说。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天寺还在,后历经火灾及“文革”破坏,才彻底圮毁,包括肉身菩萨在内的诸多佛物已不知所终。
据向坑村老人介绍,大天寺最后一任住持叫“余老三”,他修行悟道,武功过人,为人和善,村人都认识他。以前,向坑北山数十亩山地属寺产,由村民租种,每年秋收后租户送粮到寺院,住持都会热情接待。村民有难,他也会极力接济,解放前夕,村民汪叙森因家庭变故,被逼上了大天寺,寺院收纳他为寺内勤杂,供养衣食住行,直至1962年病危,才被抬回村中,随后去世。汪永法是汪叙森的曾侄,他8岁亡父后也随其叔公生活在寺中,至今他仍能清晰记得寺内的朱红大漆抱柱、六脚案桌、木鱼等佛物模样,水筒担水、火烤野果、林间挖笋等生活片段也依然记忆深刻。从寺院到向坑村途中,还有和尚坟、路亭等建筑。附近的玉龙泉水质清澈,为当时寺内生活水源。我们到达遗址时已下午两点,还需原路返回,故未去探秘这些古迹。
遗址周边除了毛竹,还有燕笋竹和水笋竹。燕笋和水笋应是以前僧人种植的,分别在前庭和后院。现在水笋还没长出来,我们拔了一捆燕笋,也算请得一点佛物了。
——————————————————————————————–
本文来源:“乡野闲谈”(黄良顺)公众号
本站已获得授权如需要转载请联系作者!
 歙县景点
歙县景点 黟县景点
黟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祁门县景点 徽州区景点
徽州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屯溪区景点 绩溪县景点
绩溪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婺源县景点 景区级别查询
景区级别查询